西西在《看小說》後記自剖,「我好像有個老毛病,看了好的小說,就想告訴別人,希望別人也看。」小說之所以好看,在於作家如何寫,讀者怎麼玩。鋪陳「玩賞」過程,變成貫串《看小說》與《我的玩具》的重要核心,是西西之眼看世界的哈哈鏡。透過這兩本專欄小品,西西告訴我們如何好好玩、盡情玩,投入體驗這個還有自由無限可能的遊戲人生。
好的玩具,是 Art Toys
Q 最近同時出版《我的玩具》與《看小說》這兩本書,皆收錄一些篇幅較短的專欄文章,對讀之下十分有趣;彷彿小說也是你的玩具,而遊玩的歷程也呈現創作思維,請問你怎麼看待「玩具」、「小說」和「創作」之間的關係呢?
A 《看小說》是我在報刊上的專欄,每月兩篇,《我的玩具》與則是後來在周刊上的專欄,寫了兩年多。兩書的後記都有說明。你說得對,小說與玩具,對我來說,是一事的兩面,是很認真的賞玩別人的創作。這兩種玩具我賞玩了許多許多個年代,對我自己的創作一定有所啟發,有所助益。我們過去的教育,在五四之前,一直不鼓勵「玩」,不敢坦白「玩」,怕被指玩物喪志,忘記工作。工作才正經。張岱那本《陶庵夢憶》,寫的分明是各種玩藝,卻先自告解,要逐一懺悔。這本書,卻是晚明小品的典範。工作和遊玩,絕對不是對立的,好的玩具,會調節、改善人的工作,令人更努力工作。玩,除了貶義,還有好的意思,玩賞、玩味。文學藝術絕對不能缺少遊戲的精神,中國的莊子是偉大的「玩家」。好的玩具,可以養志,可以勵志。陶淵明的桃花源不知外面的世界,正是抗議外面的世界,一個異托邦的地方,在那裡,你不是神仙,你還得辛勞耕作。
記得魯迅的〈風箏〉,寫於在上世紀 20 年代,還寫到「我」這個兄長發現小弟在偷偷做風箏,以為這是沒出息的玩藝,把風箏擲在地下,踏扁了。魯迅這文章寫了兩三句小弟做風箏的過程,什麼蝴蝶風箏的竹骨,還沒有糊上紙,什麼一對小風輪,做眼睛用的,用紅紙條裝飾。我以為過程是很重要的。這些細節,我以為必不可少。世故的人玩政治,玩權力,那是惡劣的玩具。好的玩具,本身是一種創作,啟發人思考,讓人參與。我們要玩的就是這種有創意的玩具。好的玩具,是一種藝術,是 Art Toys。我在《我的玩具》寫的主要就是這類玩具,都很價簾,不貴,簡單,要人參與。我嘗試描述這過程。好的小說也是這樣,啟發你思考,激發你參與,而不是被動地,到此一遊。我寫作小說,也總嘗試呈現那過程。
物是媒介,寫作仍專注於形式技藝
Q 《我的玩具》很有意思的透過你收藏的各種「物」去看到你賦予的故事,比如莫內的印象畫是捕抓不同時間的「眼睛」;紙盒劇場、火柴盒、立體書和空娃娃屋則是提供玩家一個具體空間和細節,縫紉與積木則提供手作者在一定的物質基礎中刺激創意。請問你在寫作的時候會不會有某些特定的玩具在手邊,透過把玩、縫製和文字以外的創造形式,來刺激文字創作?「物」如何變成敲開「幻想」時空的鎖鑰?
A 寫作的時候並不需要玩具在手邊,我要專心致志。某些「東西」會觸發我,但寫作就是寫作,我只能運用左手。如果我知道那是什麼東西,那就不好玩了,那會是鴉片,是毒藥。
Q 你談到自己是從看小說裡學寫小說的,重點在於留神他們怎麼寫;請問觸發你開始創作小說的關鍵閱讀經驗和作家作品是哪些?創作者讀小說,如何找到福樓拜所說的貫穿珍珠的「線」? 從何時開始有「讀書筆記」的習慣?
A 我很少再看自己寫過的小說,年紀不少,記憶也有誤。形式與內容是互動的,但要學習寫作,就要留神小說大家怎麼寫,就像踢球,你看 Henry、Zidane、美斯怎樣傳球、走位、射球,看教練的陣式、調配,而不是看球賽結果。另一方面,你知道人家寫過了,你要發展、改變,要寫得不像他們。我看文學創作,看重的是形式的創新、突破,你告訴我這小說這電影反映社會什麼什麼,好的,因為這也是一個角度,內容也可以是一種突破,但要評斷文學藝術,還是要回到美學形式去,要從美學形式去判斷,不是社會學、政治學、人類學……。我其實說不上有「讀書筆記」的習慣,那是 30 年前在報刊上寫的專欄,加上其他雜誌,後來出版了《像我這樣的一個讀者》、《傳聲筒》、《時間的話題》對話集。

小說要呈現思考歷程,文學藝術最忌簡化
Q 在《看小說》這本書裡所觸及的作家作品橫跨歐美與南美洲,甚至到印度;但這些書裡卻甚少華文作品,請問這本書裡所提及的作家作品是如何被挑選?你希望它呈現怎樣的小說圖景?
A 不能在一本談閱讀的書裡包括你所有閱讀過的書,是不?我過去,大概 1987 年編過四本中國大陸作家的書,這四本書之外,我其實在港也介紹過不少個別作家的作品,沒有編集罷了。臺灣的作家,我當年在香港介紹過鍾理和、王禎和、白先勇、黃春明、七等生……還有瘂弦、楊牧。你向一個地方介紹他們熟悉的作家,是否很怪異,很班門弄斧?當今華文作家,不如你向我介紹。《看小說》這本書不敢說呈現怎樣的小說圖景,我在後記裡解說過,不想重覆了。這是近年我自己的一部分閱讀,另一部分是西方的科幻小說。
Q 在《看小說》裡,你用昆德拉、卡爾維諾、喬伊斯、福樓拜等人的作品或小說概念,與之對讀。請問該書當中是否有哪些作家小說,啟發你對小說的具體構思?這些玩玩具和讀小說的經歷是否也在你創作各階段有不同的啟迪?
A 我的「階段」,對不起,超過半個世紀,我不想回顧,我寧願多寫幾首詩,我剛修改好了我寫了五年的長篇小說,倘有時間,我不如再看一遍。
Q 你曾寫道,小說是一種說謊的藝術,但它一邊要你相信的同時又自我瓦解。裡面談到很多篇小說寫過去該地方的歷史與文化,對戰爭、性別、種族和階級的深刻反思,也提及「非虛構寫作」本身的現實荒謬性;你自己如何以小說思考歷史、虛構和真實之間的關係呢?這與你構思「肥土鎮」的城市百年小說有關聯嗎?
A 以小說思考虛構和真實之間的關係,以具體的小說,呈現那思考的過程,本身就是「如何如何」了,譬如《我的喬治亞》,我嘗試描述整個思考的過程,從自己 DIY 一座英式微型屋,回溯香港的營造,如果小說之外再解釋,又要解釋得周全,那就是論文,而不是小說,其實也不必再寫小說。出之於小說,是避免簡化。文學藝術最忌簡化。
Q 你認為怎樣的小說才是好看的小說?它會有好玩的性質嗎?當「電影」這類視覺文本以更多細節取代想像之後,小說如何和電影對話?你寫過許多影評,未來會想出版相關著作嗎?
A 沒有一個好的答案,也不要相信這種答案。壞小說總是一個樣,好的,個個不同。我沒有想過小說為什麼應該要和電影對話?六、七十年代新浪潮電影時期,我寫過數百篇影評、影話,有年輕學者計畫收集、編輯,很好,我自己可再無能力想這類相關問題。
人生是個玩具盒,什麼不是玩具?
Q 如果你只能帶一本小說和一個玩具,你會挑選哪些?對你而言,他們有哪些特殊意義?你又怎麼看《我的玩具》與《看小說》這兩本書的特色與對你的意義?
A 什麼都不帶了。《我的玩具》與《看小說》這兩本書,是我人生的一個過程,我寫作大半生,而且一直在寫專欄,可說什麼題目的專欄都寫過,所以我特別喜歡《我的玩具》,希望我的讀者也喜歡,這專欄要是我 28 歲時寫,一定會聽到斥責,如今 82 歲,倒受到鼓勵。我不會再寫專欄。好幾次,我在玩具店看中了某件玩具,店員會說:買給小朋友,或者孫兒吧。當我說:不,買給我自己。他們會有點驚異。這在外國,從來沒有人會這樣問,因為根本不成問題。有的玩具說明不宜兒童,可從沒有說不宜成年,或者老年。有的玩具註明,適合 6 歲以下的,或者 12 歲以下的,可從沒有說以上的。我想說,到了「長者」的年歲,你還需要玩具,好的玩具。回望你的一生,生活在這小小的星球,經過許多世代的演化,宗教的、民族的,種種紛爭,何曾停止過?暖化、污染、疾病,其他物種逐一滅絕,你以為人類真有進步嗎?這麼想,你會問:什麼不是玩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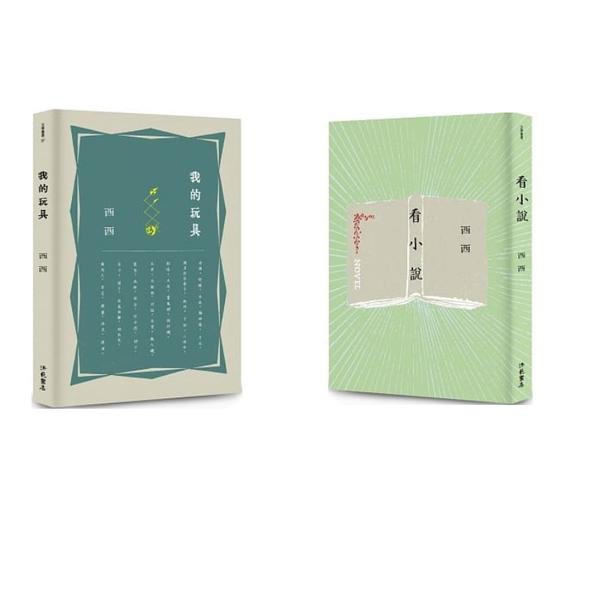
《我的玩具》,西西,洪範出版社
西西所收藏的「玩具」:維多利亞房子、水怪、羅馬尺、千花、天使、精靈、小淑女、浮士德、金絲猴、陀螺、烏篷船、聰明蛋、械人機、摺龍……
陳寧找我替周刊寫專欄,吸引我的,是可以配上彩圖。我想了一下,還有什麼沒寫過呢,有了,玩具。我一直玩玩具,可沒有寫過玩具專欄,當然,過去寫了大半生的專欄,論什麼主題,其實也只是我的玩具,我玩得很認真。對我來說,玩玩具也是一種學習的過程。設計玩具,好的玩具,本身就是一種創作。我玩的是玩具,但我欣賞的是那種創作的心靈,那是單純的小世界,讓人稍稍離開複雜,而日漸不好玩的大世界。」
「每周一篇,我寫了兩年多,往往一寫五六篇,然後交朋友發去打字,要不是自覺要變換一下模式,我還可以繼續寫下去,玩下去。家中還收藏了不少玩具可寫哩,例如摩洛哥那七個民族布偶,我自以為是鎮箱之寶;又有半米高的 3D 公仔,是洋娃娃中的精品,因為她是球形關節,用繩索整個穿連起來,結構高難度。此外,總有大小朋友送我新玩具,我精神好了去逛街,也會見獵心喜。」── 西西
《看小說》,西西,洪範出版社
「我好像有個老毛病,看了好的小說,就想告訴別人,希望別人也看。」
西西總是在看,不停地「看」,看房子看娃娃屋熊仔猿猴看玩具看世界……以無止境好奇靈敏的眼與心,持續不歇「看小說」,看看她如何看寫這五十四本小說:《魔山》、《純真博物館》、《少年Pi的奇幻漂流》、《白老虎》、《性本惡》、《包法利夫人》、《愛與黑暗的故事》、《芬尼根的守靈夜》、《我的父親母親》、《焚舟紀》……
「我的《看小說》,不是文評,真正的文評,我不會寫,我寫的,就像學生做的讀書報告。我是從看小說裡學寫小說的。寫了大半生,我仍然在學習。我看小說,一般來說,並不怎麼在意作家寫了什麼,而留神他們怎麼寫。」── 西西
採訪|李筱涵
寫散文的人,偶爾也寫點詩。現就讀於台灣大學中文所博士班。在各種生活夾縫中成為文字打工仔。曾獲林榮三文學獎,詩、散文與人物專訪散見於報紙副刊與文學雜誌。散文集將於明年出版。
撰文|西西
攝影|江田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