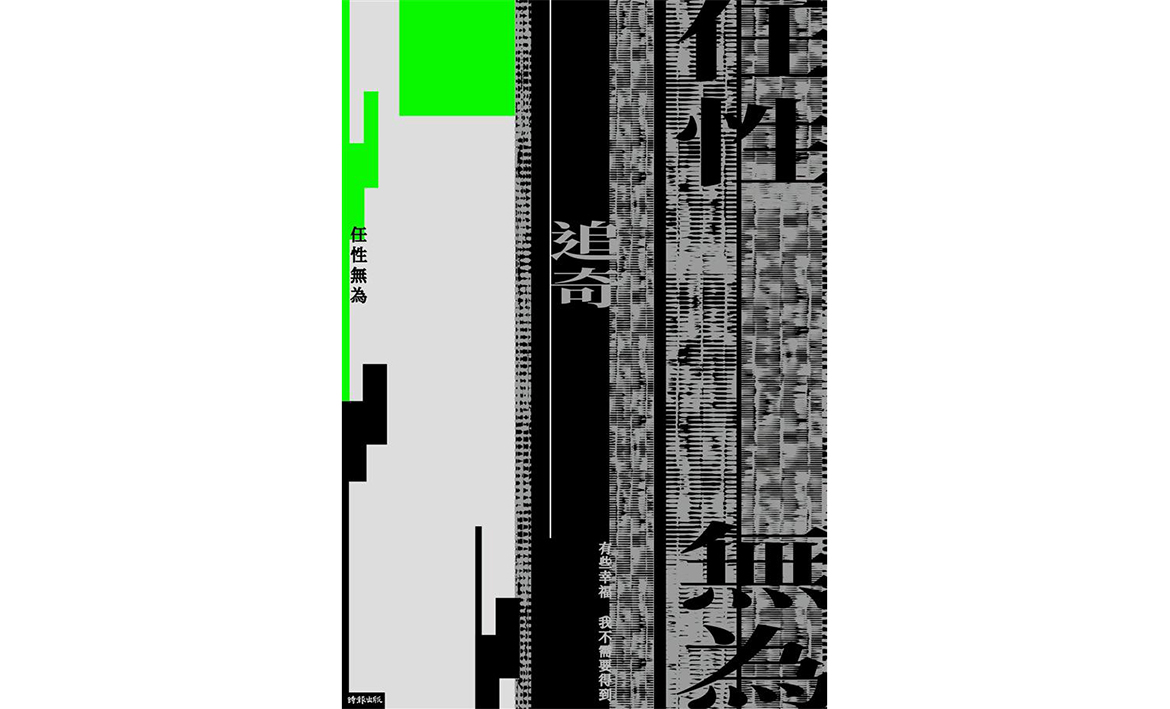《任性無為》仍維持前兩本詩集以來的寫作觀,然而,不同的是,追奇提到:「這是一本很自私的書,大部分的內容,中心全是我自己。」(博客來「青春一起讀」訪談)更多的自己,以及確實去過「地獄」,深刻體會濃厚暗黑的人生困境。由此,這本詩集可以說是追奇迄今最暗黑並散發最強烈自救意義之作。
筆者今年甫發表一篇學術論文,談論徐珮芬的暗黑系書寫,著眼於她「自癒,癒人」的詩歌效能,隨即在六月出版的新詩集裡,乍見追奇第三本詩集《任性無為》的扉頁自介寫著:「寫字是為了拯救自己,或者更幸運地,也拯救他人;雖然到最後,可能誰都拯救不了。」在當代,寫詩自救(甚而救人)的傾向為何如此強烈?
「自救」的詩人剖白,並非只出現於新世代書寫,簡略列舉的話,我們可以發現陳黎在《妖冶》(2012年)的前言中說:「我稱這些詩為『再生詩』,既再生馬太福音已有之文字,也企圖再生、復活自己身心的力量。」自我救治的意圖明顯。再把時間拉遠,曾出版過一本詩畫集《魔鬼的妖戀與純情及其他》(1985年)的小說家施明正,他在詩集後記說明自己為何要寫詩:「假如沒有使用這種自我療治的創作行為,來治療我瀕臨死亡與瘋狂的自我心理分析等,移情於詩的創作過程,……後人也就不能再看到施明正投注我的全生命,奮發創造的畚箕文學:詩與小說,和我非凡的素描與油畫」。這段真誠而重要的剖析,曾令筆者深思詩歌是如何成就其文體的特殊療癒功用。
不分年代,當詩人吐露寫詩自救的詩觀時,作為讀者,需不需要調整(或附加)欣賞角度?
在拯救的意義之前,追奇還提到「告別」:「這本《任性無為》,被我個人視作一道人生分水嶺,想以此和二十七歲的我以及二十七歲以前的我告別。」為何要告別前此的自己?因為「快樂的事一下就忘了。/憤怒的、悲傷的,隨便就想起來。/想起來後,整個人又被丟回過去。」(〈就好膽慢慢消磨〉第13首)戰勝不了過去(以前的自己),就分割吧,因而才得以保全從《這裡沒有光》逃離的僅存光亮,以及《結痂》後逐漸康復的自己。
追奇堅信:「黑暗對傷口而言,就是最好的滋養」、「悲傷是解決悲傷最好的方式」,前兩本詩集受到讀者的喜愛,有部分原因來自於她真實的分享,她絕不藏起傷口,面對傷痛,以詩開啟修復程式。《任性無為》仍維持前兩本詩集以來的寫作觀,然而,不同的是,她提到:「這是一本很自私的書,大部分的內容,中心全是我自己。」(博客來「青春一起讀」訪談)更多的自己,以及確實去過「地獄」,深刻體會濃厚暗黑的人生困境。由此,這本詩集可以說是追奇迄今最暗黑並散發最強烈自救意義之作。
此集收錄多個面向的題材,包括愛情心緒、社會議題關懷(如第五章「沒有愛就沒有違抗」為香港發聲)等,聚焦主軸則是所謂「送給自己的詩」,書寫主體身處陰暗心境裡的心情剖白。如〈暫離〉的末節:「我要我的天空多美/它就有多美/我怎麼生,又如何死/人的自主權生來就已經微渺/假使有天得以不用歸來/在夜晚,我的靈魂壞得支離破碎/也很值得」,現實太苦,靈魂暫離,寄望在夢裡累積一些不存在的快樂;〈那個人死在那年夏天,不回來了〉第二節:「只能遲到。等冬天來了又過。那個人的靈魂睡了一整場雪,埋得像沒有呼吸/屬於他身上的水都結了層冰/我赤腳踩過,使出全力空拳直落/──裂痕,卻只從我的四肢開始/迸現」,「他」是那叫不醒的靈魂、凍結的四肢,若與之對抗,徒留碎裂的自我……,這樣的碎裂形象在集中俯拾即是。其中最直捷的,當是〈剪〉這首長詩,以類散文詩式的碎唸堆疊語言,追問自己該如何被愛與自愛:「當我選中你 你會想怎樣剪我/怎樣剪我 我也可以剪成你喜歡的樣子/我才勉強活下來 被你摺疊被你黏貼被你彩繪」。主體拙於自愛,經常自厭,在第三章「她與她的黑狗」(黑狗,「black dog」,借指抑鬱)、第四章「自厭也自癒」明白表露。例如〈實心的孤獨〉有讓人心疼的自我隔離:「闔上眼/深吐氣/我反鎖每扇門窗/放正常人一場假期」、〈我過不去〉末節:「我甚不知道/一個渴望幸福的人想/遠離幸福,這是/什麼樣的病」,一種無法真正幸福的病、〈飛航模式〉首節:「我的身體裡住著一個另一隻魔鬼/比我更像我」、〈聽好〉:「淺淺劃破的皮 咬牙撕起/深深插入的刀/不要拔」……。字字句句帶著幽深內傷,卻又冀望著文字能清理,「真正需要洗淨重來的是我自己/我也只夠再穿上我自己。」(〈洗晒之訣〉)希望自己不要再被社會格式化:「很多個我,之所以半途而廢或做得不夠/是因為我明白自己/全都抵達不了。我困在路上」(〈也想被人託付〉)。
這些自傷自剖自棄,同時指控社會價值觀之禁錮的詩作,往往共鳴了讀者。加上追奇大部分的詩先發表於社群平台,篇幅不長,借助精簡用語、巧妙的節奏轉折,吸引讀者快速看完並獲得理解。近年來,「晚安詩」和「每天為你讀一首詩」,即充分發揮此優勢,若搭配情境圖或簡要賞析,更能打動人心。
回到開頭的問題,讀者既已窺知詩人自救書寫的寓意,如此真實私密而「實用」的特質,在閱讀之間,是否該有不同的閱讀眼光?抑或視作詩之主題,納為詩歌美學欣賞的一環,無須另眼?又或者,詩的書寫與閱讀早已連動互涉,詩人自救過程的文字整理,亦幫讀者整理了傷口?如同一樣收到廣大讀者回響的徐珮芬,她曾說:「畢竟我最一開始拿起筆寫字,是為了拔除自己靈魂中那些深刺入骨的利刃。當初真沒想到在治療自己心病的過程中,會得到回聲,……素未謀面的陌生人們告訴我:我把他們心中的『悲傷』給寫出來了。」(〈有時候我覺得是文學選擇了我:一個偏執寫字狂的自白〉)
暗黑傷痛之陳列,或許已成為當代詩歌的一個共相,原來詩人提筆自救,讀者也可能同時咀嚼著詩句、進行自我傷口清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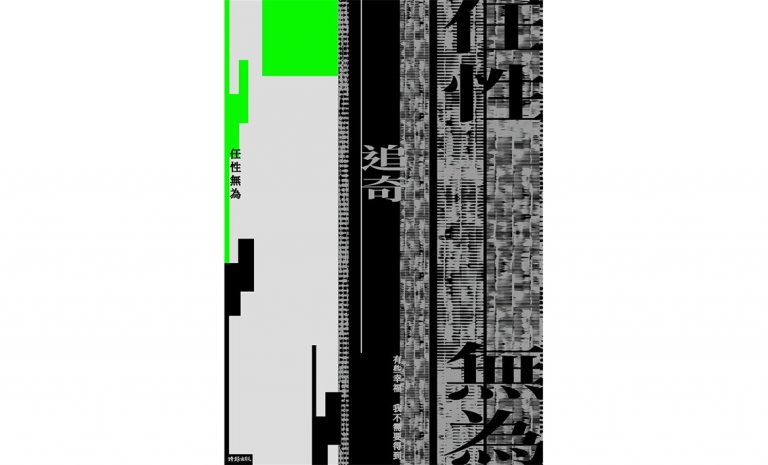
《任性無為》,追奇,時報出版
從恣意妄為 到 任性無為
從逐浪而奔 到 靜觀而安
墜落後斬獲新生,引領自我審視苦痛之意義
遂發現是 全新的世界
100首詩作
收錄私密的、跌宕起伏的情感書寫
攸關自身與他人,他人與社會
太過幸福的
教人瘋癲的
或醜陋,或拷問,或縱情放蕩
走過看似一事無成的時光
此刻再望,皆是滿載豐
文|李癸雲
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台灣現當代文學、現代詩學、性別論述。著有學術專著《詩及其象徵》、《結構與符號之間》、《朦朧、清明與流動》、《與詩對話》,以及期刊論文數十篇,曾獲數個文學獎與教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