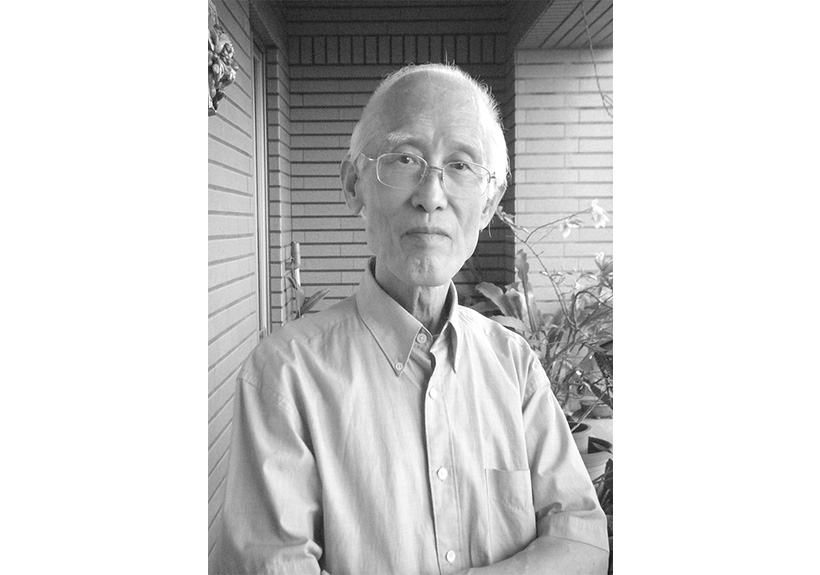「余光中」這三個字,代表著穩定一致的答案,還是更多的困惑與追問?⸺二○○五年我發表〈與余光中拔河〉一文,正是用這句話來當開頭。沒想到十二年後八十九歲的余先中因病辭世,此一疑問句似乎依然適用。這位藝術上的多妻主義者,自詡右手寫詩、左手撰文,顯然對自己的詩作最為看重。他以筆為劍,拒絕向黑暗繳械,儼然是五千年中華文化道統的台島護衛:「最後的守夜人守最後一盞燈/只為撐一幢傾斜的巨影/作夢,我沒有空/更沒有酣睡的權利」(〈守夜人〉)。這位現代詩人風格屢變、技巧多姿、幾無題材不能入詩,豈會甘於自限守夜一職?對更年輕的世代來說,余光中之「祖輩形象」是如此巨大,實為任何一部中文詩歌史無法輕易略過的景觀。晚於余光中的詩人則像一個個具有俄狄浦斯情節的孩子,想法設法要在強大陰影下另闢蹊徑,亟欲修正、位移、重構他的影響,好替自己開闢空間並擺脫「遲至」(belatedness)的焦慮。
詩人一九七四年赴港任教、一九八五年返台定居,扣除回台灣師範大學客座的一年,十年「香港時期」可謂他一生創作的高峰。代表性詩集《白玉苦瓜》跟《與永恆拔河》分別在一九七四、七九年間出版,所錄作品或懷鄉、或詠物、或述志,無不窮盡想像之妙,辭章之精,閃現著詩神眷顧過的靈光。但從年輕時便勇於介入文學論戰的他,也是在香港時期繳出〈狼來了〉這樣的黑暗文字,不管表面理由或背後故事,此篇終究成為戒嚴時期文人最壞的寫作示範。
但我始終認為余光中最大的困難,並不在敵方或他處、左右或統獨,而是要如何超越「余光中」自己?一篇〈狼來了〉不足以讓他跌下繆思的神壇,創作多重複而少新變才是其「祖輩形象」快速消退的關鍵。一九八五年余光中決定移居高雄,返台後的世俗聲譽更臻頂峰,也繳出了〈控訴一枝煙囪〉、〈讓春天從高雄出發〉這類「名作」。這些詩篇固然是地方政府推展觀光或媒體廣宣的利器,可惜早已沒有過往銳意革新、自我突破之企圖,要說是「代表作」恐怕連作者自己都不會點頭吧?從二○○○年《高樓對海》到二○一五年生前最後一部詩集《太陽點名》,他成了創作力猶在、影響力盡失的前輩詩翁。二○一一年那首引起年輕詩人群起訕笑的〈某夫人畫像〉,之所以被批評的最大原因不是政治,而是詩藝。
儘管如此,這樣的詩人「余光中」寫作成績仍不容一筆抹煞,三個字必將銘刻在任何一部台灣新詩史/文學史之上。也因此恕我無法理解,台灣著名的「覺醒青年」林致宇為何會在詩人逝世三天後說:「余光中的殞落,將會是台灣文學的黎明」。難道台灣文學在余先生逝世之前,都是一片黑暗?我實在很好奇他讀過多少余光中作品,還有多少台灣文學作品,才下得了這麼便宜的論斷。我對新世代覺青本來深懷期待,但這一唐突論斷只說明了此人既不了解余光中,更不了解台灣文學。至於對岸國台辦跟台灣陸委會爭相追悼詩人、尋求對話,只是大愚若智地在搶佔逝者便宜⸺你們這些官,又何時真正愛過現代詩呢?

(文訊雜誌社/圖片提供)
楊宗翰
淡江大學中文系專任助理教授,著有評論集《台灣新詩評論:歷史與轉型》、《台灣現代詩史:批判的閱讀》、《台灣文學的當代視野》,主編《逾越:台灣跨界詩歌選》、《跨國界詩想:世華新詩評析》等書。
◆本文原刊載於《聯合文學》第39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