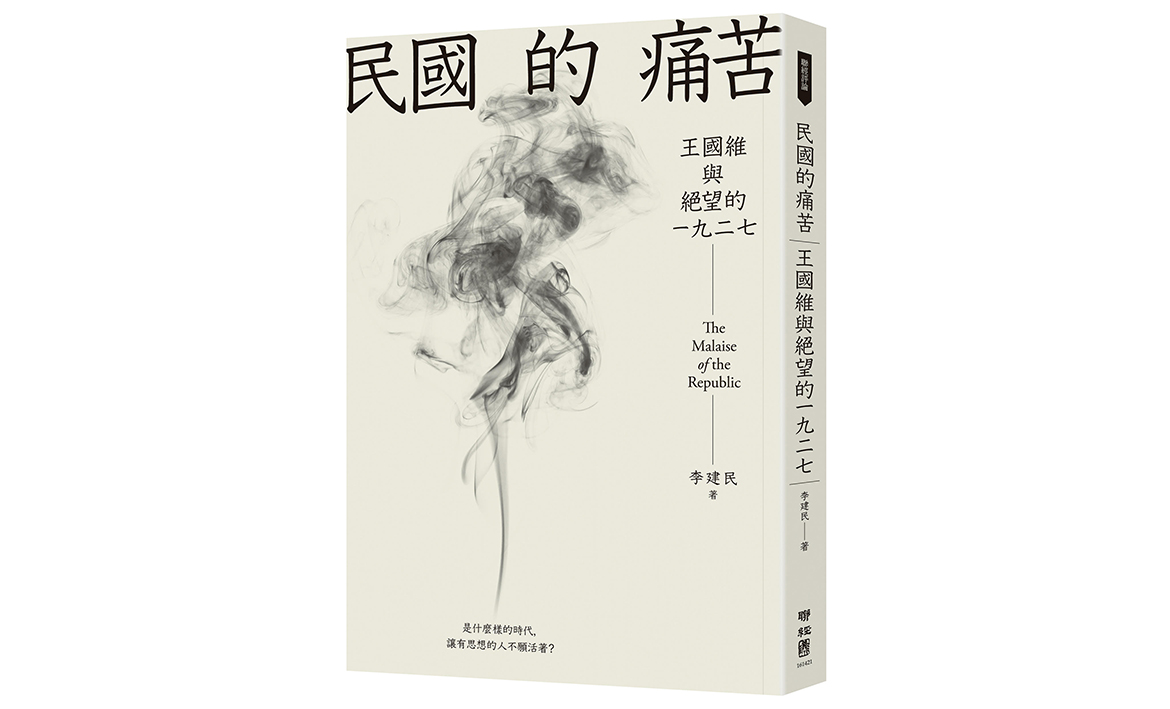王國維之自殺,一度在後世華人學子心目中有著尼采「杜林之瘋」一般的象徵意義,如某種哲學標竿。從殉清說到殉國說,到殉時代說,王國維的圖騰層層加碼,其中當以另一大師陳寅恪為他在清華大學衣冠塚所撰碑銘為巔峰,短短數行,樹立了東方知識份子的新標準——死殉自由:
「士之讀書治學,蓋將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真理因得以發揚。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這十字,即使今天讀來仍教大多數知識份子自慚汗顏,私以為此實乃陳寅恪先生於亂世臨頭時對自己的期許,因為即使王國維及其同輩遺老、或後輩先進人士,皆當不起這十字的重量。
「思想而不自由,毋寧死耳。」這句才真正道出王國維先生的悲劇。這是我讀罷李建民《民國的痛苦:王國維與絕望的1927》後無奈地承認的,王國維恰恰死於思想不得自由、精神不得獨立。這是時代普遍的精神狀況,人莫能外,但忍受不了這種折磨而自殺的,唯王國維耳,因此悲劇才稱得上悲劇的本意,而非鬧劇。
「余正告天下曰: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學之徒,即學焉而未嘗知學者也。事無大小,無遠近,苟思之得其真,紀之得其實,極其會歸,皆有裨於人類之生存福祉。」(王國維《哲學叢刊》序)先生的自我期許當然也一點都不低,而這句話的重點還在於他極端強調做學問的非功利性,但李建民著作卻濃墨重彩地點出王國維在世俗世界的功利性追求——當然也指出羅振玉所起的催迫作用。因為家累與私情,王不得不追隨羅當「文物販子」;又因為精神不獨立,王樂於當遺老、當南書房行走、伺候溥儀鞍前馬後⋯⋯最後人生也不得自由。
但李建民此著探討的不只是王國維的意義,更是自殺的意義、時代更迭的意義——「殺死王國維的那個活在中華民國的自己,就是真正的活在清代的自己」——像這一金句綜合的。王國維在其文本世界做到的、李建民此著也做到了,就是陳寅恪這句「脫心志於俗諦之桎梏」。李建民不只是為了作翻案文章,更不是寫民國逸史,他寫的是摧人肺腑的心靈史,這樣一顆心靈,我們本以為在中國近代史之濛昧裡找不到了。
也正是因為立意脫俗,李建民的文風靈動自由,有本雅明的味道:既旁徵博引又輕逸騰挪,橫向拉出一眾清末民初知識分子「陪審」,縱向招魂的則是古今中外在乎「自殺」的賢哲詩人。難得的是,作為一本史學隨筆,書中毫不避諱地無時無刻不有「我」在,顯得更像一本後設小說。這也暗示了李建民自己與王國維的共情,那就是為什麼書名是「民國的痛苦」而不是「清國的痛苦」,按理王國維只承認後者,但作為身在二十一世紀台灣的中史學者,李建民同樣能感到所謂「亡國感」吧。
不過李建民不是他書中略有諷刺的「民國遺民」,他的筆力鮮活,皆因他要紀錄的乃是人間——王國維「人間詞話」那個人間。李建民特別有提「魯迅在一九二七年紀念王國維的短文,為什麼不提到王氏的自殺?」我倒是想到周作人給魯迅的訣別書裡那句「都是可憐的人間」。
對於通曉日文的周氏兄弟和王國維而言,「人間」有著中文日文雙重的涵義(日文「人間」意為「人類」),那麼《人間詞話》豈不是《人類詞話》?想到這一層的時候,我突然想起初讀《人間詞話》時那三十年前的自己:16 歲讀他的生,46 歲讀他的死,所謂人間,不外如此。
李建民引用王國維詩詞不多,唯獨這句「若是春歸歸合早,餘春只攪人懷抱。」甫一出現,便成為了全書的背景音樂,一直哀鳴至全書終結。然無限餘緒,總是無可奈何花落去了,也許只有我們的文字,能賦似曾相識燕歸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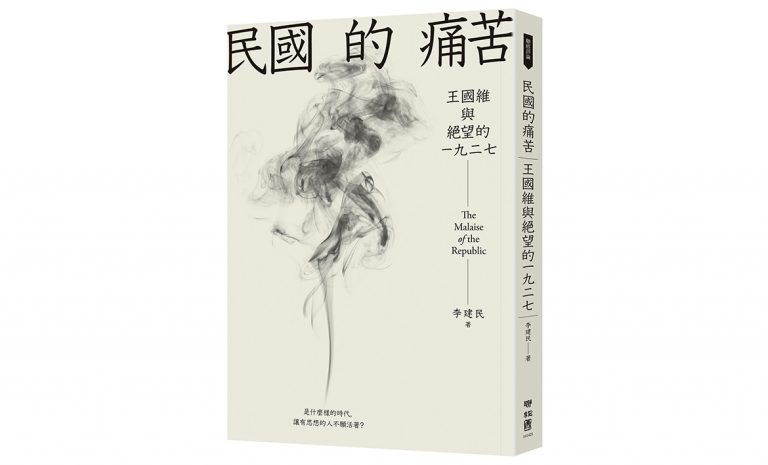
《民國的痛苦:王國維與絕望的一九二七》
李建民/著,聯經出版
1927 年,國學大師王國維在北京頤和園投湖自盡,留下遺言:「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事變,義無再辱。」身為民國初年最具聲望的學者,王國維突如其來的死亡,為當代中國知識界帶來極大震撼,對他的自殺動機,歷來更是爭論不絕、眾說紛紜。有人宣稱他是以遺老身份殉清、或為中國文化衰微而死,卻也有人認為他是經濟現實的因素而走上絕路。但人的死亡,能夠如此輕易歸結嗎?一位知識份子選擇告別人世,原因又真會如此單純?我們究竟該如何看待王國維之死?又該如何在歷史之中,理解人的痛苦?
文|廖偉棠
香港詩人、作家、攝影家,現居台灣。曾獲香港文學雙年獎,臺灣時報文學獎,聯合報文學獎等,香港藝術發展獎 2012 年度最佳藝術家(文學)。 曾出版詩集《和幽靈一起的香港漫遊》、《野蠻夜歌》、《八尺雪意》、《半簿鬼語》、《春盞》、《櫻桃與金剛》、《後覺書》等十餘種,小說集《十八條小巷的戰爭遊戲》;散文集《衣錦夜行》和《有情枝》;攝影集《孤獨的中國》、《巴黎無題劇照》、《尋找倉央嘉措》、《我城風流》、《微暗行星》;評論集《波希香港•嬉皮中國》、《遊目記》、《深夜讀罷一本虛構的宇宙史》、《反調》、《異托邦指南》系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