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晴舫午安:
在《群島》裡,當李憲宏去山上的養老院探視母親時,他「著實被母親的衰敗模樣嚇了一大跳」,「覺得悲傷,更覺慚愧」;因此,想起了深澤七郎的著名小說〈楢山節考〉。也許,在台灣比較鮮為人知的是,在發表〈楢山節考〉四年後的1960年,深澤七郎寫了〈風流夢譚〉。這篇小說,因內容有日本皇太子、皇太妃遭到斬首的情節,被極右翼的「大日本愛國黨」認定「褻瀆皇室尊嚴」。黨員之一,小森一孝,遂攜刀闖入刊登小說的《中央公論》雜誌社社長嶋中鵬二家,欲刺殺社長。不巧社長不在家。所以,他殺害了女傭丸山かね,並刺傷社長太太雅子。這就是「嶋中事件」。事件之後,深澤七郎本人,也為了人身安全,而躲藏與隱居了五年。
事件發生時,小森一孝年僅十七歲。他是長崎人,核爆時兩歲,災後倖存,原鄉成長,遭長崎東高校退學,赴東京後,被吸收為黨員。二十八歲時,在精神並不穩定的情況下,小森死於獄中。簡單說:監獄,就是這位「青年死士」十一年來,一個人的楢山。
當我們討論「極權的起源」,小森,是我一下會想起的原型人物之一。也許,就像無數「青年死士」一樣,他深信是黨、也只有黨的義理,能賦與在現實裡頗挫敗的他生命意義,及個人價值。是的,小森也「想要屬於一個偉大東西」。關於戰後日本極右翼意識形態,如何寄附於對戰爭無罪免責的天皇體制之中,坊間的分析很多,我就不贅述了,只想旁注一件我們已知之事:恐怕,無論時代遷演,這種「犧牲體系」(高橋哲哉的理論)內,CP值最高的換取,總是它能用虛構的「偉大」,來讓人自願、且還備感榮寵地交出自己的生命。
而其實,對我而言,這整件事還有一個難以逼視的面向,即那位真正無辜的犧牲者,女傭丸山之死。我不知道她的身世,因為什麼原因而在社長家幫傭,是否,為了保護社長太太而死。我不知道在那致命一刻,丸山如何對視小森。然而,我但願這個空洞,可以是人間一切堂皇話語的楢山。
於是可能,當我們討論「共存」,我們事實上深切思考的,是事理難能無傷周照的實況。一如當我們討論「自由」,我總想起小說家胡淑雯的透徹之言:
「我覺得解放僅僅在於,人知道自己為什麼不自由,我覺得我們沒有自由這件事情,沒有真正liberation,根本就沒有自由這麼純粹的事情,人最多最多只能夠解放到,知道自己不自由了,而且知道自己為什麼不自由。」
邊際廓清。我個人認為小說創作珍貴的意義之一,即是耐煩地,尋索並探究上述的「為什麼不」。這當然也是為什麼,如前信所言,我覺得你的小說承載了比作者明確主張的,更複雜的語義;或者,一種能夠立體化作者主張的反義。是以,我仍想標註你的《懸浮》裡,我很喜歡的〈春夢〉這篇章。其實,喜歡的理由可以很簡單說:在近年來我所閱讀的小說裡,它是極少數的幾篇,讓我見識到人的情感仿擬能力,可以恐怖到什麼地步的好作品之一。
你看:在〈春夢〉裡,「我們」預支與馴養我們不可能經驗的死亡,以為享樂;購買有愛情調味的肉體服務;置身自己,於一座無有晴雨、卻一定有空調和熱水的水晶宮內;且反轉宮外沙灘,為攝影棚般的景片。如果能夠,「我們」會動員親歷與未歷的一切,只為暖化自身的孤獨。而這一切,多少只證明絕對自由之不可能。也許,一如死亡,它們都不是人類經驗。
但對我而言,理想的小說證明上述「不可能」,是何等的不可能。是為小說能觸及的「反義」。
(這裡偷用了傅柯的語言邏輯^^)
敬祝 週末愉快
p.s. 謝謝Carpe diem, quam minimum credula postero。
活在當下,盡量不要相信明天。我剛剛突然想到如果像之前假設:時光機造出,人回到過去即導致世界末日,那是否意味著:人乘著時光機到未來,其實是一種自殺行為?
對不起,冷笑話。
偉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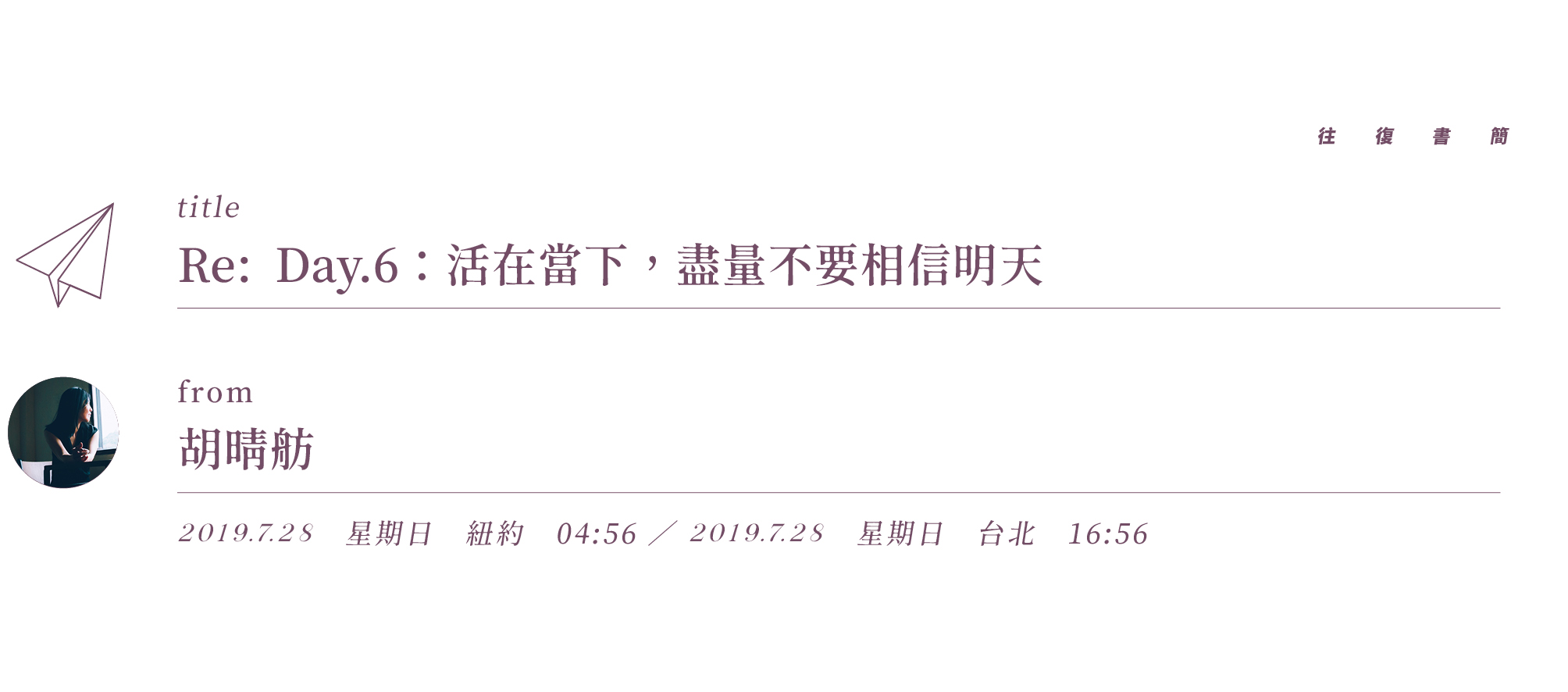
偉格,
我對人性的理解始終落在自由與不自由的中間,不自由有時(可以)是自由的形式(或產物)。毛姆寫過一本小說《人性的枷鎖》,我先假藉書名來說明我的文學見解。
我以為,相較於現代社會科學對人的處境慣性使用的總體分析,古老的文學賦予(或承認)了一個人更多的自主能力,除了他一出生的社會處境他無法決定之外,不少時候,就算在社會條件嚴苛的情況下,他會(他能夠)做出屬於他的選擇,而因為他的選擇,他之所以為他,不是別人。文學探究每個人的動機。相同的生命處境,每個人對應的方法都不一樣,而這個決定來自個人,那是個選擇,這個選擇使得你我不同,反應了你我的性格、性情,價值觀,也就決定了你我分別的命運。文學承認人有弱點、缺陷,充滿錯誤,面對他的命運,他未必是完全被動的無辜者,但不代表讀者不會帶著理解的眼光同情他。費茲傑羅《大亨小傳》裡偉大的蓋茲比,他的悲劇可以說他愛上了不該愛的人,可以說是階級衝突,但,蓋茲比之所以是蓋茲比,來自他處理他對黛西的愛的方式,他如何透過黛西想像了另一個自己,而拼命去實踐,結果他只是「假貨」。讀者同情他,因為讀小說時,看到了自身的種種缺失以及夢想的遺落。同樣在狄更斯的《雙城記》裡,一個動盪不安的革命時代,愛一個人的方式竟然是,在對方毫不知情的情況下,替對方所鍾愛的人去慷慨赴死。這些都是出自個人面對生命處境所做出的自主選擇。
我應該是因為自己的生命經歷,開始明白世上大部分的人比蓋茲比更悲劇,儘管他們在自身人生也是有許多掙扎與痛苦,對史家或小說家來說,他們卻完全不值一書,他們被賦予的平庸來自於他們甚至沒有故事性,因此注定不是個角色,賺不了點讚數,譬如「嶋中事件」的丸山女傭,她只是剛好在那裡,她就被殺了。她最具「現場性」——她也只有現場性——故事在她之前展開,輾過她的生命,故事在她之後繼續前進。以個人自戀的視角,每一個人都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主角,重要得不得了,但到了網路上、歷史洪流裡,他人指尖一滑,便消失於宇宙不知哪一個黑洞裡,若要全然依賴他人的認知系統來刷存在感,這當然是極其恐怖之事。
我是重度科幻迷,所以我對時間旅行特別好奇,對你的冷笑話完全不會等閒視之。終究,時間旅行依然關乎時空的相遇與交錯。小說處理時間題材,我極愛姜峯楠中篇小說《你一生的故事》,後來改編成電影《異星入境》(Arrival, 中文譯名多可怕),因為英文文法分過去式、現代式、進行式,以英文寫成的小說一開始,讀者馬上掉入時間迷霧裡,明明是未來才會發生的故事卻用過去式來敘述。當外星人為人類帶來所謂的『禮物』,即預知未來的能力。即便一瞬間已經知道了過去、現在與未來,一個普通的人卻使用了她的自由意志,做了她的選擇。說起高超寫作技巧,我想起馬丁艾米斯(Martin Amis)的《時間箭》(Time’s Arrow),整部小說倒著敘述,像一部電影倒帶著看,不再屈服於前因後果的推理,人生盡顯荒謬、世間果然愚蠢,我們已經活在自己一手創造的異星球。
一大早我從中央車站步行至中央公園,從西 72 街搭地鐵下哈德遜園區,沿高線公園往南走向世貿中心,橫過曼哈頓南端,最終坐在布魯克林大橋下吹河風。中途,下午三點,我坐在西村的一間家常餐廳裡,借他們的網路,閱讀你的來信,那一刻,我其實沒什麼明確的時間感。時間畢竟是人類發明出來的概念,藉以計算我們在地球上活著的軌跡。今夏正好是人類登陸月球五十週年紀念,這兩週美國電視重播了許多當年的實況畫面。迄今,仍有很多陰謀論者宣稱人類不曾登陸月球,那些影像證據只是在美國內華達州一處沙漠拍攝的。或者,我們熱切關注的登月紀錄真的只是三個叫阿姆斯壯、艾德林、柯林斯的美國男人的露營照片,不曉得為什麼並不干擾我對登月這件事的想像,我們其他人都不曾真正登月,因此都只能透過想像。請容我再用另一部科幻電影《星際效應》(Insterstellar)作為這封信的結尾,為了要解救地球於糧食危機,父親拋下兩名孩子,志願前往太空尋找可供人類居住的新星球,一次意外使得他掉落於第五維度超正方體,他突然明白了,在遙遠的未來,人類已經克服了過去、現在與未來的限制,當他看見他遺留在後的女兒正站在自家客廳書櫃前,他推落一本書,引起她的注意。我以為那是很美的意象,是了是了,這不就是人類社會一直以來的溝通方式?我們共享並繼續共創一個日益龐大精密的人類知識體,憑此,一起努力去克服生存這件事。但,也許,有一天,因為一次時間旅行,來自人類遠祖、而不是外星人的細菌,毀滅了我們?
這邊天要亮了。早安!
晴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