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及中國七○後作者,徐則臣自是最受人注目的一位。出身北大,創作不輟,幾乎就是背負著許多人期待的中國文壇明星,一個中堅的位置、扛著中國文學前景的大旗、也備受評論者的好評,此些年來,其創作更自覺性的挪用起各類關乎社會的議題(郝譽翔也有類似的判斷);如《跑步穿過中關村》(2008)的賣假證社群、假借主人公發聲議論、欲將「七○後」代際詮釋囊括於己的《耶路撒冷》(2014)、動用海歸教授與庶民百姓矛盾的《王城如海》(2017),這樣的創作軸線,顯然是想要扛起中國社會描摹的圖景。一個開初由小鎮青年、成長小說起家的創作者,踏上了匯合個人與群體,或將群體吞併於個人,簡而言之,就是「中國國族」的使命。
新作《北上》(2018)浩浩湯湯,就長度與內容而言,又是一本類若《耶路撒冷》的作品。文案也擺明了道:「一個民族的秘史。」針對著申遺成功的京杭大運河,虛構與紀實,鋪演相關於運河的人事與歷史,顯然是發掘與張揚著,那可為中國人驕傲的遺跡(即小說中所言:「祖先的土地」)。它的一個最顯眼的特徵,便是體積。《耶路撒冷》四十五萬字,《北上》少說也有三十萬字,彷彿見其企圖心。連帶而來的問題是:那這樣的作品是如何結構的?聲稱要寫一條河的流向及民族的命運,創作者又是如何寫起?透過這麼大規模的文字,創造出了什麼?
說實在,這本書四百餘頁,耐著性子看了一百五十頁,我就無法看下去,要不是為了寫書評,為要負責起見,大可以就此判定;但即使看完了全書,原先的判定依然相同。而且讀這小說幾乎毫無樂趣。一個可見的特徵是:所有的人物都像是作家本人的代言,幾乎無有什麼價值衝撞,有的也僅止是一種類型的遊戲。這部小說比較像個筐子,創作者想要講什麼,就直接放進去,或用類型般的人物呈演說明;幾乎沒有折曲,就是直線式的一通到底(《耶路撒冷》也差不多是相同的),不稍時就看到跳出來角色、但也同時是作家對於各種事物的說明與認知(添加了大量科普知識,而多處毫無轉化:這位小說家似乎渾然無所覺,讀者要看到的不是知識,而是作品)、他的個人信念,與各般可說是理想主義者的哲理教諭(借用作者愛說明自己的詞)──在一定程度上,這也約莫是創作者為什麼可以這麼快速而大量生產作品的原因,只要構框成型,靶子已經畫好,剩下來的工作就是把內容與細節填加進去而已。
小說來回於幾個不同的時點,但大抵而言分為民初與當代兩個時點,來回穿插。以各般簡單的類型人物:單純而熱愛中國、心有嚮往的外國人小波羅(他喜愛馬可波羅。而這設置顯然強調中國的光榮感,強調一部分的「悅納異己」),對著照相機、新事物感到驚懼的鄉野人民(即《西洋鏡》),胸懷壯志的知識人、曾經的漕運翻譯員謝平遙,想要攝製《大河潭》運河紀錄片的節目負責人、謝平遙的後代,持守跑船營生、固執但又敬謹的老船夫邵秉義……一干人等輪番上陣,表演起連結古今的戲劇,而處處充斥著顯明的寄寓。它用各般藝術與對話,自相說明起小說的狀況、與個人欲表現的關心(如「我喜歡慢。有時候慢未必是慢,可能是快,只是我們沒看出來。就像舊有時候並不是舊,而是更新。」頁209)。用各種的比喻,如記者與攝影,來照出一條河上的風景。表面上,小說在內容中曾刻意提及《清明上河圖》,但它其實缺乏那種全景掃描的細膩,一個個安插的,均是刻意為之的演劇(遠不及沈從文),要父子衝突,即父子衝突,要勾陳反洋情緒,即衝突而起,將之化為布景──作家還曾經高揚道,中國當代文學創作的形式探究不足;然而這本要作為某種時代想像與見證的作品,其功底不知道稱不稱得上寫實主義(還是稱為類型劇即可?),但無論如何,似乎毫不曾意識到,在現代主義的視野裡,以這樣的認知與關懷、這樣的世界觀,實在不需要耗費這麼多的文筆。沒有哲學。把一小點撐開,敷衍成作品,意義是相當有限的。作家想要講的東西,不必然需要用這麼長的篇幅處理;長篇的體積,不必然有著相對多的容積。就是與十九世紀的寫實主義小說相比,以我而言,這本作品也缺乏了種讓人沉浸的魅力。
就一個局外的觀察者而言,自《耶路撒冷》(2014)而來,本就位居中心的徐則臣,似乎更堂而皇之地站上了中國文壇的中心,亦展現了旺盛的創作企圖。但其實,再怎麼張擴發揮其議題,背後的世界也是相仿的,它無有孔隙,無能歧出(甚至鑿痕處處),只是成全於一個大主體的格局。歷史該當如何表現?在台灣曾經喊著超越國族與建立國族的聲音並起的這些時節,彼岸的作品,至少在徐則臣與現居於香港的葛亮的作品,我以為他們倒是對於中國的主體,居之不疑──都刻意用各般機緣巧合,讓歷史的物件傳承,得而延續。徐在《耶路撒冷》與《北上》開先,都安排民族主義式的激進人民,而讓主人公彷彿與之隔離。但這樣的寫作姿態,恐怕也與一種民族自覺的姿態無異,縱有再多的分身,也只是一個個複製,將所有的資訊,吸收入自己的囊袋;這樣的寫作,總是依據著自身的企圖,逕自催動,並以為加大「中國」的行旅,承著那集體的水勢,往前航行,便是如此而已──識者不信,姑舉一例:小說中的一位敘事者,說他製作影片時,寫了旁白這麼一段:「這個鏡頭讓我想起了敬業、忠貞和相依為命,讓我想起了不忘初心、方得始終,讓我想起了命運、光芒和不廢江河萬古流。」(頁131)而他說,這樣的文字,能把「送盒飯的劇務都煽哭了」,可是真的嗎?我不太相信,局外人看到這段(恐怕肉麻得緊的)表述時,能有相同的心情。那也就是作家小說的常態了,反正在那樣的大主體世界中,要初相識的女性愛上滿嘴油滑的男性,就讓她愛①;要讓人為了偉大的江河哭泣,就讓他哭泣。可不是如此?只要體積足了,主題看來宏壯了,關乎那偉大的國度,外邊總有人,總有支撐的體系,可以聲稱,這樣的作品,有著多大的格局。
註:
①徐對於女性的描繪,以及其恐怕是男性中心的世界觀,當另文論證處理。
文|黃健富
暨南國際大學中文系博士候選人。著有《傷、廢與書寫:童偉格小說研究》、〈無聲之聲:幾個斷片,讀袁哲生〉、〈掙脫負累,或反身的看見——房慧真散文中的主體與視界〉、〈此界‧彼方:七年級小說家創作觀察〉、〈誰能在漫長的旅途中得到安慰──讀路內《慈悲》〉、〈我,和另一個我:曹寇《屋頂長的一棵樹》〉等論文。曾獲磺溪文學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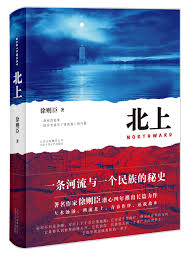
1 comment
剛開始看,覺得還蠻好看的,可能是評論者不喜歡徐則臣的書寫方式吧,我是很喜歡看他的小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