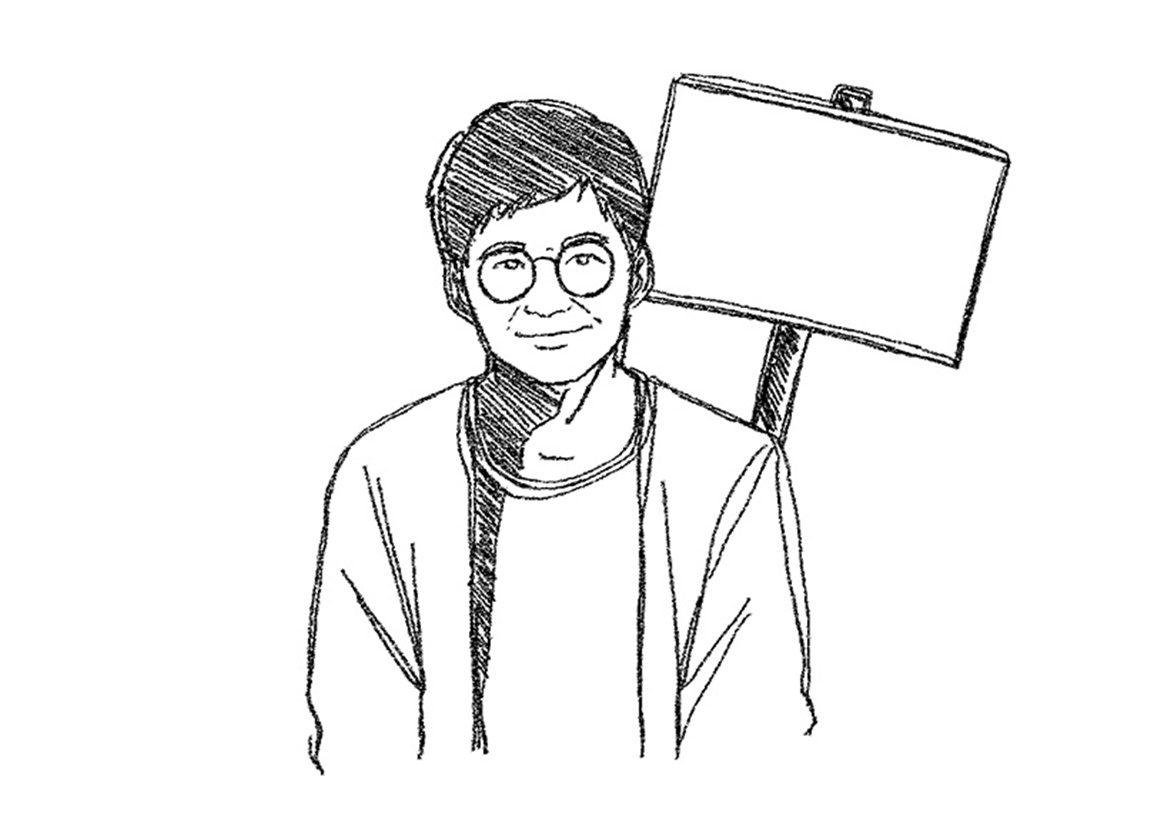他並非刻意要坐上捷運,只是發現一個捷運入口便隨人群走下,而且在擁擠的捷運上他感到安心,覺得自己不被注意。就在他站立的位置斜前方,有一位長滿落腮鬍,穿著格子毛料襯衫的洋人,像極了勤勞的北美清教徒,與一名台灣女人緊貼坐著,那女人穿著仿冒廉價蛇皮的高跟短靴,黑色的針織外套附人工動物皮毛領子,一付華貴而且太熱的樣子。他們本來像一般朋友似地聊天,沒多久就開始親吻起來,先是像小雞一般地互相啄著彼此的臉頰與嘴唇,很快便伸出舌頭,但畢竟是在捷運上不敢太過囂張,他們的舌頭微微吐出,伸進對方的唇間,稍微地,無聲地吸了一口。他覺得自己最近寫作的靈感有些枯渴,跟生活的窘迫無關,要借錢的話,隨便跟父親伸手一下就有了,只是單純有些提不起勁,大概報刊雜誌給的稿費太低的緣故。不過或許可以從這對情侶寫起,寫成一篇小說,這麼想的時候,他們忽然排開人群下了車,他想跟蹤他們,反正並沒有特別要做的事,但一出了捷運站他便在人群中失去了他們。
如此失去了今天唯一的目的之後,(即便是臨時才定的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他沿藝品店、美術用品店與餐廳酒吧的廊下閒逛,看見許多的店的門口陳列著打折的假貨古董,沒有光澤的冰冷玉器、學藝不精的文人仿畫與紋飾拙劣、形制失真的陶瓷,經過一家新開的酒舖之後,一條巷子裡他看見一家咖啡館,他一走進去便感到後悔,不過又是一間複製了其它間咖啡館的咖啡館,一樣的圖書館燈、一樣的木頭人造皮桌椅、一樣的左派人物與王家衛電影海報、一樣的抗議標語布條、一樣的遊行通知傳單,書櫃裡堆滿了一樣的文學品味,他坐下來,取了兩本最近大受歡迎的小說,比較老的那個作家寫了一本只是放大過去的風格讓自己變得更像自己的小說,比較年輕的那個作家則寫了一本濃縮過去的風格讓自己變得更像自己的小說,簡單來說,就是把複製的尺寸改變一下的程度。然後他點了咖啡,在菜單上寫著是某款南美洲的某莊園的某批次的某烘焙度的某處理法的得了某獎項的某名字的咖啡豆,穿著黑色圍裙梳著髮髻的咖啡師端來一小杯咖啡豆與磨好的咖啡粉讓他聞,並問他是要用手沖的,(濾紙或法蘭絨)還是用法式濾壓壺、摩卡壺、虹吸壺、Espresso機或是smart7手沖機器人(內鍵世界冠軍設定的參數)沖煮呢?「有不同的風味與價格。」咖啡師說,「當然。」
他最終還是充滿偏見地選了機器度最低的濾紙手沖,他覺得這樣或許最有可能發現手工的「靈光」乍現,即.使.是在這個為了讓虛假的意識型態產生效果,只好用複製又複製來強化的咖啡館裡。而在他等待咖啡端來的片刻,天使忽然來了,說是來了,也只是坐在他的對面,一句話也沒說。明明人家一句話也沒說,只是眼睛歪斜地看著他而已,但他覺得天使在嘲笑剛剛失戀的他,(看那缺牙微張的嘴)嘲笑他過去災難般的人生,也嘲笑他跟廢墟一樣的未來。
他(沒什麼理由地)發怒了,刷地站起身,正向天使揮出弱弱的一拳時,咖啡送來了,他只好坐下看著窗外正要推門進來的人,他覺得,那一瞬間有些中國古典的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