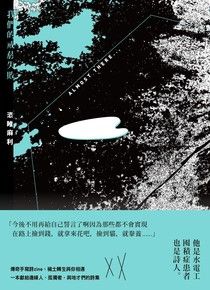作為異岸讀者的我,當然是先在網路上讀到恣睢麻利的新聞。在這個同時因網絡影響而著重隱身又同時講求背景來帶動閱讀興趣的時代,恣睢麻利或者會是一個巧得兼美的人物——他既有種深邃的神秘,而又帶著極繁富的背景鮮明強烈地現身於讀者眼前,一個或者不算恰當的比喻是,像駱以軍的小說語言風格直接擬成真實的人。他的水電工,及陰暗情緒生活,加上囤積癖所連帶的外在部分,在在劃出世界所不能完全穿透的陰影部分。
是的,我對囤積癖是近乎沒有抵抗力的。我是反收納者,又喜歡留著所有小小的無意義的證物,信封、包裝紙、發票、電影票、傳單、別人的喜帖、便條、外賣單、鈕扣、破拖鞋、穿破的衣物、不知連接何物的電器線……但我用盡方法把囤積癖局限於囤書,此即我所不夠徹底之處。想起《大佛普拉斯》中灶財的家,黑白影像中那個無限魅惑如仙境的「飛碟」,也陳列著灶財夾回來的無數娃娃。欲望在都巿中的耗費,體現在底層人群身上的變形反而有一種真實的魅力。我竟是從虛構世界去理解真實存在的恣睢麻利。
《我們的戒菸失敗》始於手印詩集的形態——只印了百來冊流傳甚少,未嘗得見實物,不知道它真的是像現在的小開本詩集書腰中所稱的「zine詩集」潮物,還是如舊式小量地下油印詩集那種粗糙而憤怒的成品,我是略略比較傾向後者的。無論是橫向的社會向度,還是縱向的歷史向度,憤怒都具有其普遍性。一般人理解憤怒,多由現實與社會維度切入,惟我喜歡憤怒,乃是因為憤怒與藝術結合時,會出現一種強大的創造力。
恣睢麻利的憤怒不是那麼顯性,因為詩中的憤怒對象不是那麼明顯清晰。就拿最應該憤怒的〈豪宅〉來說吧,一個底層人士寫及豪宅,豈不是有足夠的理由憤怒?但詩以一枚眼鏡的鏡仁作結構上的牽引,多次觸及身體意象與空間意象的互換;鏡仁抖落,「向上拔擢的大樓結構接住並包覆它/鏡仁從此與鐵石無異/那些大樓都是用尿液和膝蓋去灌溉/夕陽照耀在城巿和它的工業」,大樓被身體的意象滲入、改變、汙染,工業的光輝背後是身體的污穢堆疊而成。「我」的鏡仁本是「我」與空間連繫的中介,在一天「我的鏡仁離我遠去/去成為一座豪宅」,在這裡詩人轉而使用「風景」、「美好」等字樣,用一種兩不相干的漠然中稍帶奇異的溫婉語氣說,「那些大樓都蓋得好漂亮/在我們不常經過的路上」。
如此漠然輕盈的語調因一種距離得而產生,而這種距離又恰恰指向相反的東西:詩與詩所憤怒的對象,已經部分溶合。距離指向的是融合;詩人經常在一些關鍵時刻改變主意和態度,脫離他人的預設,在該憤怒的時候吹起口哨來——一如在該馴服的時候扭頭抽身而去。恣睢麻利的詩有流淌性質,但那是金屬的流淌,堅硬與液態同時共存,未知於其定向。如果工業時代是集體是規律,則恣睢麻利的工業則是個體工人之角度:金屬熔合,燒焊,變化,拼接——工人專心致志於物質狀態的轉變。同樣的結構也見於〈是夜班〉、〈工人未滿〉等作。
轉變乃由行動帶出。但有趣的是,恣睢麻利的詩中,行動與行動的目標是脫節的,即行動多半無法達成其目標。行動只指向無序的改變。以行動之無定向變化,當數〈說愁少年;四號阿丁〉,「關掉視窗」、「複製貼上」,以至「每日擦亮鏡子在多班制裡踱步」,全部不指向任何收獲,一如惡夢醒來時發出的「不具意義的咿嗚聲」。與目的脫鉤,行動就是純粹無意義的生之能量揮發。恣睢麻利的詩裡有馴服與不馴服,達成與未達成,像〈每日的天氣〉中,「你」叫「我」做的事全都做了,但都是無意義的,一刻一瞬間就揮發了,談論過去時句式不免帶著些許依戀的模式,但「其實你想說的只是其實而已」——這結句乃是極力想把意義取消,留下一個模糊極簡最MINIMAL的手勢/姿態/示意。無意義的行動指向句子意義的互相勾銷,只有純粹的變化漫衍。
或者是我的迷信:無意義的詩有時最能見出詩人的天才。因為無意義的寫作需要某種內在的直覺判斷去維持整個結構,一鬆懈便散落一地不成片段。而恣睢麻利的詩有某種強烈的藍調歌謠感覺,他用身體意象與空間意象互織,日常打屁句子與詩意強烈的書面語體混貼,關鍵還是一種都巿的節奏,生活的節奏。因此儘管詩人拒絕一清見底的意義,卻有著藍調樂手的鮮明姿態。
關於歌謠關於工人,幾乎到口邊的是一句「勞者歌其事」。傳統認為,被壓在社會底層的工人文學,應該歌詠其工作生活,產出平民的寫實的詩歌。恣睢麻利也交出「後工業時代」的「工人詩」:勞者歌其事,事曰心事,非指純粹外在的社會性事務。恣睢麻利的詩裡面,內在抒情的佔比還是高於外在描寫與遭遇的。寫給舊情人阿秋的〈留給我的〉中「突然想起多年前你忘了關火的那壼開水要是還在就好了」,這一句的敏感躍進,非常觸動人。且不愧於生在這樣的金句時代,恣睢麻利像這時代的李歐納.柯恩,充滿著金句:「片刻上頭的億萬年砂粒安息在我的指甲縫裡/要過多久才能不讓人感覺羞辱」(〈空的悠遊卡〉);「就這樣全速前進吧/雖然是爛掉的果實/若飛行於太空中/也是會變成流星的啊!」(〈乘客〉)
以水電工的身份去概括恣睢麻利是不足夠的;作為囤積症患者,他也實在太傾向於出走與行動了。工人的詩,並不等同身份。我想起香港的一位詩人飲江,也是多年的電工;但他的詩,卻總以玄妙與哲學思考見稱,並在瞬間進入永恒億萬年的時間維度,至此讓人覺得談他的身份,都太渺小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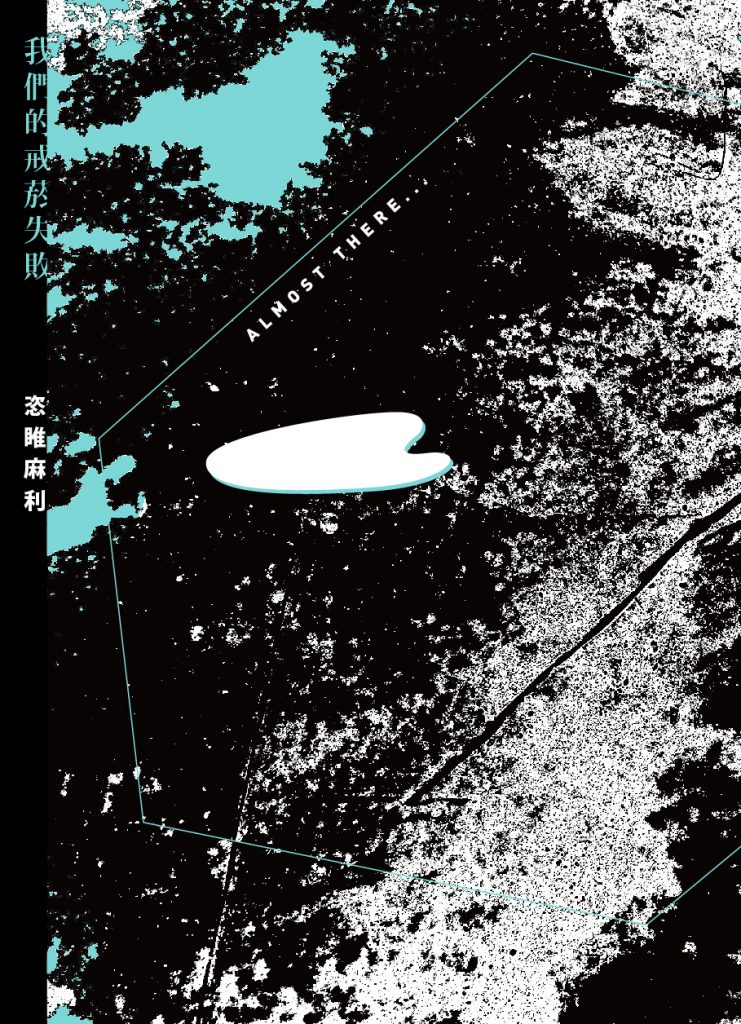
作者:恣睢麻利
出版社:逗點文創結社
書籍介紹:
在滿是記憶符碼的、擁擠的房間裡,他曾提筆抄詩,聽著傷心欲絕,用一台小影印機,列印出略帶無力卻又奇怪積極的白紙黑字;使用訂書機裝訂後,再以電火布(水電膠帶)封邊,做成一本名喚《我們的戒菸失敗》的zine詩集。很粗糙,就這樣,全臺灣100多人擁有,卻幾乎沒人願意割愛。
鄧小樺
香港詩人、專欄作家、文化評論人。著有《若無其事》、《眾音的反面》等。香港文學館總策展人,文藝復興基金會理事。港台電視節目「文學放得開」主持人,於各大專院校中兼職任教,2014獲邀參加愛荷華大學國際作家寫作坊,亦曾參與台北詩歌節、亞洲詩歌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