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耀明長篇鉅作《邦查女孩》,以透明純淨的文字,描繪壯麗的台灣山林風景。在傳奇式的筆法中,勾勒出溫柔而感動人心的愛情故事,帶領讀者返回七○年代,見證台灣林業興衰的美麗與哀愁。

陳明柔
東海大學中文系博士。曾任教於暨南大學中文系、南華大學文學所、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兼系主任。現任靜宜大學台灣文學系副教授。曾主編《遠走到她方:台灣當代女性文學論集》。
甘耀明
目前專事寫作,小說出版《神秘列車》、《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殺鬼》、《喪禮上的故事》、《邦查女孩》、《冬將軍來的夏天》、《成為真正的人》,與李崇建合著《對話的力量》、《閱讀深動力》、《薩提爾的守護之心》等教育書。著作曾獲臺北國際書展大獎、開卷年度十大好書獎、臺灣文學獎長篇小說金典獎、金鼎獎、香港紅樓夢獎決審團獎、金石堂十大影響力好書獎。
一座森林, 如何成就溫柔的愛情
陳明柔(以下簡稱陳) 讀完甘耀明的《邦查女孩》,最大感想是:非、常、好、看。我認為,這是用一整座森林,來成就一個溫柔的愛情故事。
甘耀明(以下簡稱甘) 編輯說,讀到結局很揪心。其實,我想傳達的是關於生命的告別。
陳 我覺得,這也是從愛情的告別當中,用詩質的語言來寫一個時代的告別,帕吉魯把山留給山,再從山裡走出來,沿路不說「回頭見」,而是說「再見」,這是對時代的離別。
《殺鬼》的議題複雜,有國族、文化認同、新鄉土,文字則是被摺疊起來,讀者在閱讀時要把文字逐一剝開,才能理解背後賦予的多重摺疊的象徵密度。而《邦查女孩》既寫實又傳奇,文字滿溢山林氣息,這是一篇山野傳奇,書寫鄉土的新里程碑。
至於女主角古阿霞與男主角帕吉魯,兩人的身份也極有意思,是互為「轉譯」的對象。帕吉魯患有阿斯伯格症與緘默症,他的語言只有古阿霞能讀懂,而山林的話語,則是藉由帕吉魯轉譯給古阿霞,角色塑造十分有趣,不知道此兩人是否有何原型?
甘 帕吉魯與古阿霞,在某種程度,是《殺鬼》中的帕與拉娃的轉世,彷彿前世今生的襯映。比較不同的是,《殺鬼》中的愛情是躲躲藏藏,而《邦查女孩》中的男女愛情,則是拳拳到肉的真槍實彈。
七○年代, 台灣現代化的轉捩點
陳 小說背景是台灣的七○年代,你也將「現代化」的經驗嵌入了小說之中,為何情景選擇此年代?
甘 我在寫作的初期,苦苦摸索如何下錨時間點,總是下不到錨。我最初是將小說設定在六○年代左右,所根據的史實,是摩里沙卡(林田山林場)在民國六十一年發生森林大火,以及日本明治神宮的世界最大鳥居原木由台灣的丹大山輸出,若要符合以上史實,主角古阿霞的年齡會不符小說內在的需求。最後,我決定將時空打破,先不要管特定時空,而是把摩里沙卡融合為台灣山林開發的混和型平台,於是阿里山、大平山都是小說取材對象。此外,取材的歷史事件,也包含中日斷交、中美斷交、中共與美國建交,以及對花蓮後山有重大影響事件,那是北迴鐵路在一九八○年的開通。因此,我最後將小說的時間點,定調在七○年代末。
之所以寫七○年代,因為此時正是台灣走入現代化社會的轉捩點,如十大建設、鐵路電氣化等等基礎設施,經濟上升,加快了山林資源走向潰竭之路。時代的設定,決定小說外在的張力,這個年代的歷史成為小說的「景深」。

甘耀明創作關鍵詞(一)
・千面寫手
甘耀明出版第一本小說集《神祕列車》,集結了歷年囊括各大文學獎的短篇小說,書寫類型包含青少年成長、諷刺時事、政治思辨、武俠、仿古說書、都市情感、鄉土傳奇……等等風格,文字顏色七彩斑斕、新穎多元,文學評論家李奭學獻上「千面寫手」的封號:「每讀完一篇,我總覺得甘耀明好像就換了一個人似的。」
・文筆可驚天
「甘式語言」另一種特徵,在於辭藻的華麗多變,以及意象高密度的表現。甘耀明文字最大特色,便是擅長使用譬喻法、轉化法、以及誇飾法等等千變萬化的修辭法,讓小說充滿爆炸性的文字力量,為故事情節增添光怪陸離的趣味與戲劇張力。因此,中國作家莫言稱讚三十萬字的《殺鬼》是一本「如此文筆可驚天」的長篇鉅作。
・客家民俗
甘耀明父親為客家人,成長於客家庄,熟習當地民俗文化,從小也在家鄉苗栗獅潭聽聞諸多鄉土野談以及家族史話,因此下筆創作小說時,也自然融入了濃厚親切的客家文化,講述關於鬼神、信仰、傳說的客家民俗,在寫作中加入客語呈現,但展演方式也能讓非客語讀者融入故事情節,創造出獨樹一格的「甘式語言」。
・失憶的鬼
甘耀明提及《殺鬼》中的鬼,「不是陰魂之類,而是內心的遲疑與徬徨」,描述了人們靈魂的墮落與昇華。在後殖民理論中,「認同的焦慮」是被殖民經驗中難以跨越的柵欄,甘耀明筆下的鬼與人,不只失名也失憶,在流轉的時空中,被剝奪名字的體驗,就像是一再「被殺」的噩運輪迴,最終忘卻自己究竟是人?是鬼?
重新思索: 台灣伐木業的共犯結構
陳 我有感受到小說家藉由扭曲時空的力量,重回歷史現場。小說揭露了台灣現代化的過程,很有意識覺醒的意味,當然這種意識是後設的,二十一世紀的此刻重新去解讀當時。也就是,你帶著二十一世紀的眼光,回到七○年代,在構築小說的過程,也讓讀者理解當時的伐木狀況。例如台灣的林業史,曾經是個共犯結構,政府與業者是集體的山老鼠。
甘 小說家的另一個能力,就是解釋歷史,賦予現代感。若要寫歷史小說,是否要完全遵照歷史?見仁見智。或者,用現代的眼光,帶著讀者去重新認識歷史事件。小說其中一位角色「素芳姨」,擁有現代登山倡導的環保意識,這種概念在七○年代還未普及,如陳明柔老師所言,當時的政府是帶頭砍樹賺錢的「山大王」,哪重視保育。我在小說添入這意識,是從現在觀點切入。
我讀過賴春標先生的報導,他是台灣重要的森林保護者,他找到泰雅老獵人傳說中的棲蘭山「扁柏神殿」。扁柏神殿非常迷人,我小說中「咒讖森林」有一部分便是依此創造。一九八八年,賴春標在《人間雜誌》發表了「來自台灣森林的緊急報告」,他深入丹大山林區,調查民間木業在兩千五百公尺海拔以上超限砍伐的違法行為,賴春標將此事詢問官員,官員卻支吾其詞。他因此下結論:這是政府與民間的共犯結構。隔年,迫使退輔會刪除了伐木預算。
因此,我對山林環境的關照放在小說,重返當時情境。來自丹大山林區的孫海是個吃素的人,做慈善事業,不過在那個年代,他是靠政府撐腰伐木。當時他從西部來到了小說中的菊港山莊,所講的一席話,代表了伐木工的無奈,以及森林砍伐不得不為的心境。
陳 這種現代感,是小說家帶著文字扭曲時空、重新詮釋的眼光,回到現場。我也發現時空設定中,滲透在小說中意識覺醒的意圖,透露了你凝望台灣當代感的視角。閱讀的同時,也不會有任何的違和感,小說中的情節、角色都十分合理。
透明的文字, 純淨的語言
陳 除了賦予意識的再生,回望七○年代來構築小說,另外有一個重要的元素是:文字。
把大敘事、歷史事件嵌進小說的時間軸,要好看,卻不匠氣,很考驗功力。而你的《邦查女孩》則擁有很溫柔的故事脈絡,我覺得之所以會迷人,便是在於文字的氣氛。從你過往的作品中,能讀到很詩質的語言,也有俚俗、方言的運用,而新作品中的文字則很節制、很透明,你以往的文字具有多重摺疊的濃稠性質,但新作品似乎在告別那樣的文字風格?而這種語言透明的純淨度,則形成了閱讀流暢度的推進。
甘 完成《殺鬼》之後,我在校稿出版時意識到,書寫風格會干擾某些讀者,閱讀進程會在某些地方會卡住、攪繞。沒錯,這就是風格。如果《殺鬼》重寫就不會寫成這樣了,然而時光無法逆轉,《殺鬼》停在不可逆轉的特殊風格。在寫《邦查女孩》時,我思考要採取什麼樣的風格,如果要與讀者有比較好的溝通,又要採取什麼樣的形式?寫了《喪禮上的故事》,那樣比較鬆軟的講故事方法,也影響到我。
《邦查女孩》最初始的文稿,共有四十七萬字,看來十分臃腫。小說完成之際就是另一個苦難的開始,因為要我刪稿,要幫女孩做減肥運動(笑),後來刪到四十二萬字。這過程反覆在哪要刪、哪要留,都是考驗。當我回想《殺鬼》造成的閱讀狀況,便痛快的幫《邦查女孩》削肉。我刪除不必要的枝節,包括將近一萬字的某章節,關於古阿霞與帕吉魯在南橫關山隧道的故事。當時辛苦寫的小說,在最後重新整理時,凡是意識到會卡到的細節,全刪除。
小說太長了,為了與讀者流暢的「溝通」,我也做了一些調整,如分行的方式更細緻,也多增加一些對話,小說節奏該快則快,該停頓則停頓。在主角兩人的動作上,則增加了彼此的「凝視」,因為在《殺鬼》中,動感很強,《邦查女孩》也有動感,但希望能讓讀者有多一點「凝視」的空間。
寫《殺鬼》背景即便是日治時期,我的語言調性仍是很現代感,我將自己定位為一個說書人,後設的敘事聲音,可以用一些現代感語彙,塑造閱讀時「時空既遠、腔調又近」的語氣。在《邦查女孩》中,我同樣使用一些現代的詞彙,例如,七○年代不會使用「八卦」這兩字,但小說中,我描述菊港山莊的女性長舌,還是「八卦」比較傳神;小說標題所使用的「PK」,也是現代語彙。我如何考究都無法還原七○年代的氣氛語言,就依照我設定的想法寫,但有個原則,在對話中不要使用現代才出現的語詞,當然也有誤用的。
我另一個敘述策略,則是在某些枯燥的細節,加入幽默口吻,讓小說變得有趣、有彈性。


陳 《殺鬼》的閱讀上,可能會造成遲滯,一座一座的小山丘必須越過,不過也構成了甘耀明小說的旅程,你如同文字的魔術師,讀者必須要很專注,才能把文字打開,看到更多的意象。而你的新作品在文字經營上的節制與刪減,形成了閱讀上流暢的好看,對於小說中山林故事、愛情故事,都是必要的形式,《邦查女孩》的閱讀感受,與《殺鬼》是截然不同。對我來講,新作的語言飽含一種潔淨度、透明感,是小說迷人之處,尤其在描寫山林間,是一種「靜中帶動」的場景書寫。如一開始破題時,古阿霞在木瓜溪說到她族群的神話傳說,山中動物轉變成植物的有趣意象,即便是安靜的森林,也充滿抒情的流動質感。也因此到了結尾我非常感動,讀到某一位主角在休克前的夢境告別,決定離開森林,這一段極度抒情,感動人心。
甘 我的登山導師歐陽台生,對於山林有非常深刻的感受,他曾在玉山國家公園做過幾年公務員,後來厭惡僵硬體制,要離開大山之際,內心惆悵,心想可能再也不會回去那個所愛的地方了,於是他從玉山頂花了三天走到塔塔加登山口,沿路跟所有認識的植物、動物、每一個往昔曾碰觸的事物告別,說再見。我聽到這個故事之時,充滿感動,多年後成了《邦查女孩》的結尾旋律。
對於小說中的結局,我思考了很久,所謂告別形式,究竟要怎樣寫呢?後來我採用了比較抒情的方式,跟森林的扁柏們告別,深情撫摸,角色帕吉魯選擇這樣的告別,人對自然多情,想必「青山見我應如是」。
在當代文學中, 自我的定位
甘 當時會開始寫作鄉土,我也不清楚產生的動念,或許是因為現代主義小說、酷兒小說、女性主義……等等類型,建立了經典,塑造了一道牆。作為創作者,要有所突破,只好找新題材與風格。不過在台灣,從三、四年級以來,精銳的小說家們都在寫嚴肅文學,我反而鼓勵七、八年級的小說創作者,不一定要硬擠到這舞台,當今的書寫類型很多,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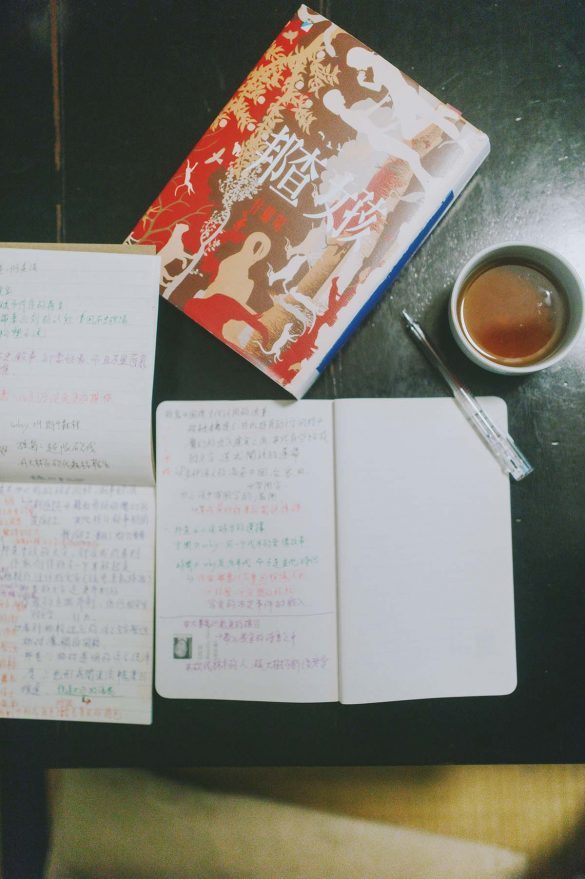
甘耀明創作關鍵詞(二)
・國族認同
論述「記憶」,常將創傷經驗、被壓抑的潛意識作為連結,甘耀明《殺鬼》的「歷史記憶」,便是國族認同議題的再思索。對於認同的困惑,以及身分的多重矛盾,造就台灣歷史魅影重重的面目。小說展現了過往台灣被壓抑的困境,而「集體記憶」的重現便是串聯各篇章的重要線索,不論是日軍來台、皇民化政策、國民黨來台、二二八,皆呈現文化認同的辯證。
・新鄉土
九○年代之後,以鄉土為題材的作品,不同前代鄉土文學強調族群使命、社會問題,新鄉土傾向將鄉土視為舞台的提供,以翻新、顛覆、甚至趣味橫生的敘述手法呈現當代的生存意識,描述傳統時空與現代文明的矛盾或協調,並且注重多元族群與生態意識的層面。甘耀明的鄉土標誌,體現於「鄉土知識」的運用、以及鄉野奇譚的色塊拼貼。
・成長小說
甘耀明常以少年少女為主角,呈現青少年人格成長、世界觀定型、自我認識的意涵。如《水鬼學校和失去媽媽的水獺》四篇小說,第一人稱敘述者都是幼童、青少年,散發出強烈的「成長故事」、「青少年故事」濃郁氣息,符合成長小說類型裡,對於「啟蒙」、「教育」、「成長儀式」的議題討論。在情節中,青少年主角逐步建立自我人格與價值觀。
・魔幻寫實
拉美魔幻寫實主義試圖挖掘現實底層蘊藏的神秘之處,但實際上是具有強烈政治意圖,揭露戰爭與集權政府的荒謬,所謂「魔幻」其實是現實的殘酷再現,魔幻寫實借用神話、迷信、靈怪,以象徵、誇張的情節反映歷史的軌跡以及人類的內心世界。甘耀明擅長以魔幻寫實筆法,設計怪異的人物,演出奇情怪誕的鄉野劇場,呈現台灣鄉土與歷史的多重意義。
整理、關鍵詞撰寫|何敬堯
小說家,臺中人,畢業於臺大外文系、清大臺文所。寫作主題包含奇幻、歷史、推理、妖怪。作品曾獲全球華文青年文學獎、金石堂年度十大影響力好書、臺文館好書推廣。美國佛蒙特藝術中心駐村創作、中正大學駐校作家。作品曾被改編為音樂劇、手機遊戲、桌遊。歷年著作:《妖怪臺灣》、《妖怪臺灣地圖》、《妖怪鳴歌錄Formosa》、《怪物們的迷宮》。
攝影|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