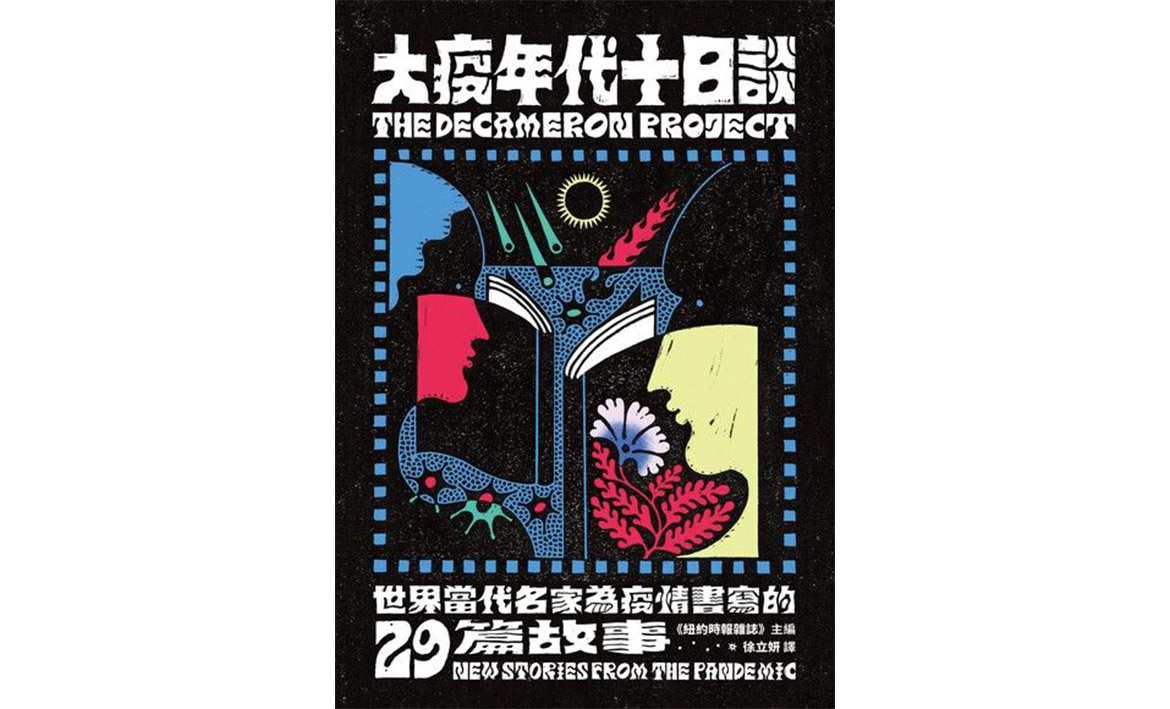天災人禍之際,人們可以在哪裡獲得身心安頓?我建議,小說是提供庇護的選項之一。《大疫年代十日談:世界當代名家為疫情寫的29篇故事》就是一個近期的極佳範例。2020年全球疫情爆發,人們心力交瘁,幾乎不可能讀寫小說,或從事其他藝術活動;但是也有人卻在小說找到浮生的寄託,不但體驗人生可能一再創生小說,也體會小說可能一再延續人生。
《大疫年代十日談》顧名思義,跟文學經典《十日談》致敬。兩者都是瘟疫促成的故事集:《十日談》中,一群人為了逃避疫情,只好躲起來,圍在一起交換故事解悶,簡直像是一個戒菸戒酒的「成長團體」;《大疫年代十日談》中,二十九位作家為了排遣疫情之苦,被迫居家隔離,分散世界各地,像是成長團體的虛擬線上版,也同樣交出故事。在古早的《十日談》到近期的《大疫年代十日談》之間,各種瘟疫在歷史長流一再浮現,也一再催生一波波小說奇葩。
台灣讀者其實早就知道瘟疫和文學的緣分。早在COVID和SARS之前,我們就已經領教愛滋帶來的壓力。COVID跟愛滋很像:我們熟悉的台灣防疫團隊(羅一鈞等人),以及美國今日最著名的防疫專家佛西(Anthony Fauci),本來就是愛滋防治的老手。1980年代愛滋在美國爆發之後,美國、台灣以及世界各國陷入恐慌,卻也不約而同在文學和藝術尋求安慰。人們都說台灣1990年代的同志文學黃金時期要歸功於1987年的解嚴,但我一直認為,我們反而應該上溯到1980年代初期的愛滋焦慮。正因為疫情燒炙人心,所以作家、讀者、愛滋當事人都轉向書本以及其他藝術,尋求安頓。
愛滋以及各種疫情,證明一個詭異的定律:疫情未必扼殺小說,反而可能激發人們更緊密擁抱小說。為了說明這種奇妙的歷史傾向,我啟用「報復性小說」這個說法。因為疫情逼人太甚,全球民眾一有機會喘息,就投身「報復性消費」、「報復性旅遊」,以及「報復性小說」。為了充分說明什麼是「報復性小說」,我在談論《十日談》和《大疫年代十日談》這兩部短篇故事結集之餘,也想到卡繆的長篇名作《瘟疫》。《瘟疫》篇幅宏大,比篇幅短小的故事更能夠廣泛觸及群體與個人的多元面向。
法國作家卡繆為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以《異鄉人》和《瘟疫》聞名於世聞名。1947年出版的《瘟疫》描繪阿爾及利亞濱海城市奧蘭的鼠疫,簡直預告了2020年和2021年的全球慘況:因為鼠疫,奧蘭官員斷然封城控制疫情;因為封城太突然,家庭和愛侶在沒有預警的情況下被拆散;人們無法回到封鎖的工作場所上班,失去生活重心;因為預期匱乏,大家搶購並且囤積民生物資。
疫情帶來的巨變將人拋擲到孤獨的黑洞裡。為了平緩孤獨感,人們更加需要「人與人的連結」。在1940年代,人們依賴傳統郵政通信。但奧蘭民眾再也不准寄信——因為信紙可以帶著細菌突破封鎖線。為了滿足與人連結的需求,大家上門泡酒館,以便證明自己仍有存在感。人們也湧入電影院,重看一再重映的老電影。上電影院乍看跟與人連結無關,卻促成奧蘭民眾跟法國維持連結。當時阿爾及利亞屬於法國殖民地,法國算是阿爾及利亞的「內地」。疫情打斷兩地的互相依存關係之後,奧蘭民眾卻可以藉著在電影院觀看來自法國的電影,腦補奧蘭跟法國之間的同步連線。
因為科技發達,今日疫情底下的民眾比1940年代的《瘟疫》眾生更加浮誇:人們擁抱「報復性消費」和「報復性旅遊」,用來抵銷一波又一波的消費不便(因為店家被迫關門等等因素,所以消費不便)和行動不便(既然出國旅行已經出局、國內旅行經常停擺,居家隔離更是家常便飯)。此外,我認為「報復性上網」和「報復性工作」也成形了:民眾再也不必寄出信紙給親友,卻可以全天候掛在網路上面跟陌生人交換疫情謠言;不必上電影院跟世界同步,卻可以在網路串流平台追趕韓劇進度。疫情固然逼迫工作場所暫時關閉,甚至拉高失業率,卻也有人趁疫情不便出門之際,加倍拼命賺外快:他們化為打工仔,接單外送食物,當網紅誘人刷卡贊助,結果比疫情之前更過勞。
有些人開始呼籲民眾克制各種「報復」行動、改用「永續型旅遊」或「感恩式消費」度過疫情難關。但我覺得這些良心呼籲似乎誤解了字義:報復型消費等詞的報復,是指「變本加厲」、「加倍奉還」,有死裏逃生的感嘆,也有溺水者爭取換氣機會的意味,跟「仇恨」、「毀滅」未必有關。
上述種種另類報復,也可能換個角度促成永續和感恩。因此,我樂見疫情催生出「報復性小說」:指疫情期間,人們變本加厲投入小說懷抱的行動,包含閱讀小說也包含撰寫小說的行為:因為人們不能上街上班,所以終於被迫面對自己累積已久卻從未碰過的書堆;也因為人們身心不安頓,所以終於甘願抄經,或是寫日記寫書法,甚至開始寫故事。跟充滿聲色刺激的「報復性上網」相較,「報復性小說」提供更加紮實素樸的慰藉。在疫情期間,網路固然提供情報,卻也餵養我們巨量假訊息、不分性別各種專家的「男性說教」,以及從政客到家人祭出的情緒勒索。電腦網路的疲勞轟炸在疫情期間更加猖狂,但只有文字沒有影音的小說世界仍然寧靜。而且,跟K歌、聚餐相比,讀寫小說本來就是特別便宜的娛樂與休息,窮人也負擔得起——畢竟,二手書和稿紙價格低廉,甚至可以免費索取。
《瘟疫》的角色之一就是藉著每晚寫稿維持身心平穩,《瘟疫》作者卡繆自然也藉著撰寫這部小說面對世局的荒謬。《大疫年代十日談》的諸多故事也揭示疫情如何誘導作家深呼吸,重新勇敢認識亂世。例如,《使女的故事》作者,科幻小說巨擘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在〈沒耐心‧葛利薩達 〉這篇小說中,描寫一個外星人在疫情期間看守一批又一批地球人。這個外星人外表頗有「克蘇魯」神話角色的風格(也就是很像電影《異形》中的怪物),試圖用俗爛的童話安撫被迫隔離管理的地球人。中國出身的小說家李翊雲(Yiyun Li),雖然在美國獲得文學獎肯定,但也受盡文學光環帶來的心靈磨難。她的〈木蘭下〉寫出因為疫情所以增加更多變數的家人生離死別。近年來美國文壇聲名大噪的台裔作家游朝凱(Charles Yu),在〈系統〉堆疊的字句彷彿來自網路瀏覽器吐出來的搜尋結果,暗示網路使用者從人類蛻變成機器人的異化過程。《雲圖》作者大衛.米契爾(David Mitchell)在〈若希望就是馬〉,則展現防疫的隔離制度強化種族歧視,並且將眾生推向妄想的深淵。
卡繆《瘟疫》指出,在疫情陷入苦戀的人很幸運,書中那位孤獨的寫作角色也自認好命,因為他們忙著戀愛或忙著寫作,所以不至於全心全意擔憂疫情。報復性文學提供庇護,並不是讓人逃避現實,而是讓人持盈保泰:在大難臨頭之際養足力氣,才得以在適當時機重出江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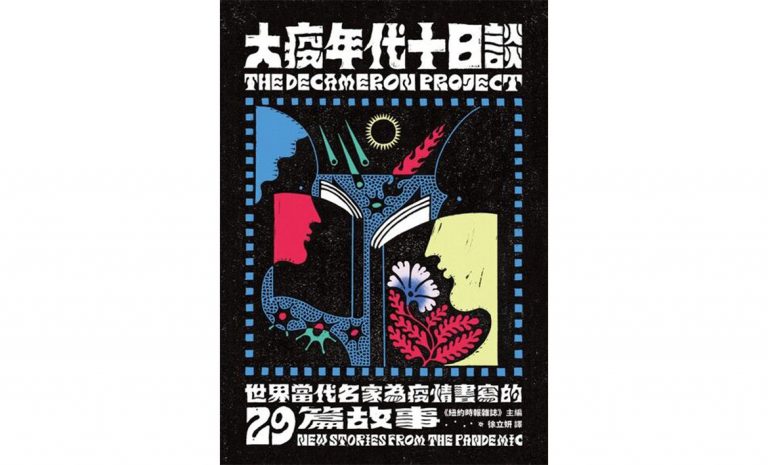
《大疫年代十日談:世界當代名家為疫情書寫的29篇故事》
紐約時報雜誌/編,徐立妍/譯,木馬文化
在《十日談》中,薄伽丘寫到一群男女為了躲避瘟疫而遠赴郊區,抵達後,他們決定每晚講一個故事好度過這段艱困的日子。《紐約時報雜誌》(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便以此為發想,邀請了數十位當代知名的小說家來為2020年突如其來的Covid-19疫情撰寫故事。無疑這是一本在疫情下最能夠反映我們心境的小說,它標記著我們這個年代,透露出了新聞中我們看不見的恐懼、破滅與希望。
文|紀大偉
國立政治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助理教授,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比較文學博士。著有學術專書《同志文學史》、小說集《膜》(已有日文翻譯版、法文翻譯版)等,雜文集《晚安巴比倫》等。IG:taweic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