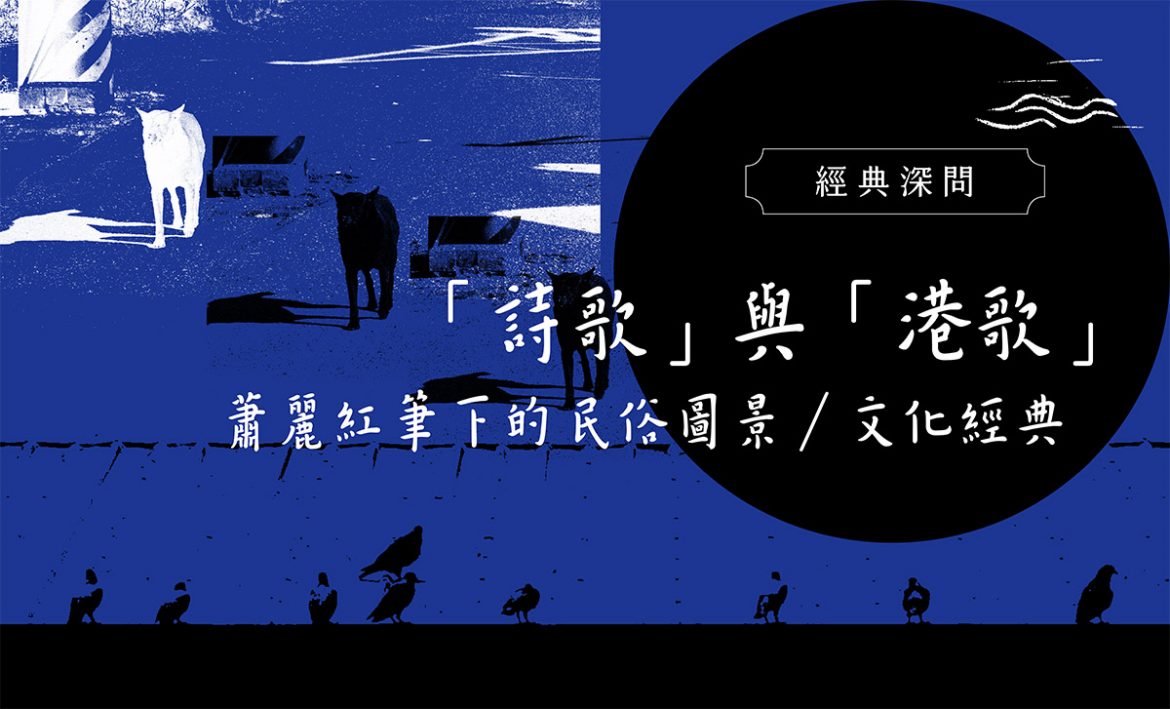言及台灣文壇最受讀者青睞的作家,蕭麗紅(1950-)無疑榜上有名:她的《桂花巷》(1977)與《千江有水千江月》(1981)都是跨越世代的長銷書,皆已成為文學史上的經典長篇。出生於嘉義布袋,蕭麗紅的故事大多環繞這座偎靠著西部海岸線的純樸小鎮展開,情節則大抵在小鎮世情變與不變的對話或對抗間演進;而秀麗有之、壯闊有之的故鄉風景,不輕易流俗改變的原鄉人情,乃至女性看待世間的有情視角與應對世變的強韌生命力,更是蕭麗紅情有獨鍾的題材,也是讀者深為她的故事所吸引的重要理由。上述特色在《千江有水千江月》中發揮得淋漓盡致,這部小說從女主人翁貞觀還在娘胎—因她在母親水紅腹肚內待了整整十二個月才願意出世(時為一九四九年),被傳為趣談—說起,隨著敘述的推進,貞觀逐步長大,行跡由嘉義、台南而至台北;不過在台北(此時為一九七二年前後),她與青梅竹馬的大信戀情悲劇收場,而正當墜入失戀低谷的時候,緊接而來的是外祖母的撒手人寰。返回布袋奔喪的周折中,貞觀有所領悟而下定決心:「她要快些回去,故鄉的海水,故鄉的夜色;她還是那個大家族裡,見之人喜的阿貞觀—」(頁375)①
整體而言,《千江有水千江月》是一部由女作家所寫的女性成長故事。此一現身說法的主題寫作在戰後文學史上迭有佳構,《千江有水千江月》之前就有潘人木《漣漪表妹》(1952)、季季〈屬於十七歲的〉(1965)、康芸薇的〈十八歲的愚昧〉(1968)與李昂的〈花季〉(1968)等形象鮮明的作品,與蕭麗紅相近的時期也有朱天文、朱天心與蘇偉貞等,先後交出《擊壤歌》(1977)、《淡江記》(1979)、《紅顏已老》(1980),乃至《未了》(1982)等重要的小說、散文結集。而在這一脈絡裡,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的特殊之處在於,她嘗試將女性成長故事與布袋小鎮的風土民情深刻、有機地結合在一起。這種結合不只體現在敘述形式上對於情景交融的追求,故事主題與人物形象依照城鄉性格來打造,更由參雜了大量台語詞彙的語言風格來實現。不過雖然描寫的是台灣(女)人,述說的是在地故事,《千江有水千江月》在這塊土地的人情世故上投射的,卻是(作者或敘述者認為)亙古不變的中國「情」境。在貞觀(或者蕭麗紅)看來,台灣民間的按照節氣而施作的習俗,大家族有禮有節的應對進退,所顯示的不啻扎根於「中國」本源的民族精神。





前行研究有關蕭麗紅的「台灣—中國」符號學已累積了頗多討論,②簡單來說,我們大抵可以依循兩條航道來定位《千江有水千江月》文體和意向的淵源:首先是興起於七○年代的「回歸現實」潮流,落實在文學界即影響深遠的「鄉土文學」運動;其次,由「三三」社群創造性繼承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它強調詩書禮樂教化的可能與必要的論述也發揮了巨大的作用。這兩股浪潮在七○年代的文學場域中都扮演顯著的規範力量,而兩者一方面都涉及此間攸關「認同」(identity)的探索意欲;另一方面,它們其實也涉及常民生活型態—主要具象為「城VS.鄉」、「大家族VS.核心家庭」的兩難—的變遷轉型。前者在小說中,主要藉由受過良好現代教育的貞觀與大信,其人的直接述說(to tell)來揭示,他(她)們尤喜在對話、內心獨白,或往來的書信中斷言此或彼現象具有「(中國)民族性」。後者較常透過人物形象或情節走向來顯示(to show),譬如移居台南市、變得「不和不悌」的五叔公,與留守老厝、信守兄友弟恭的外公與三叔公(見「四之二」),乃至執意分灶(裂解為「核心家庭」)的小表妗,與仍恪守大家族規範的外家(見「五之一」),更別說貞觀遊走於嘉義、台南與台北後的感想,這種對比的模式乃是《千江有水千江月》戲劇衝突的來源。
在新與舊的對峙中,《千江有水千江月》毋寧更同情既有的秩序,蕭麗紅在此作中娓娓道來對於原鄉故土的鄉愁—李昂的「鹿城」故事(1972-74),以及中篇小說〈殺夫〉(1983)恰與蕭麗紅的戀舊形成尖銳的對比—而有趣的是,《千江有水千江月》在表達女主角愁懷時,大量倚賴了古典抒情文學「敘述文」與「抒情詩」交織互涉的技巧;不過這個特徵非侷限於表述鄉愁,貞觀在認定某事流露民族性的時候,也經常「以詩為證」。其實《千江有水千江月》的許多橋段都隱隱流露對於抒情傳統的瑰寶《牡丹亭》和《紅樓夢》的致意,例如貞觀偶然聽見收音機傳來「春天花蕊啊,為春開了盡—」,忽然「魂飛魄散,心折骨驚」,竟至領悟了「情字原是怎樣的心死,死心」(頁97-98)這段情節明顯脫胎自《紅樓夢》二十三回林黛玉「牡丹亭艷曲警芳心」。而同一回的寶黛「西廂記妙詞通戲語」也轉化為《千江有水千江月》中,貞觀和大信兩人透過詩文、戲曲輾轉告白一己情意的情節。不過有趣的是,貞觀所聞所見而有所感的不見得全是來自中國抒情傳統的詩文,相反地,更多時候能夠在無意間觸動她心弦的實為充滿草根(本土)色彩的歌仔戲,或者台語流行歌,例如日治時期傳唱下來,表達閨怨的〈春宵夢〉,乃至失志男人吟唱的「港歌」〈港邊惜別〉。③
中國的「詩歌」與台灣的「港歌」交織互涉,款款吐露女兒對人、對「鄉」的心情與志向。這許是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之能跨越時空,感動不同世代讀者的理由。
註:
① 蕭麗紅,《千江有水千江月》(新北:聯經,二版九十刷,2019)。
② 比如齊邦媛,〈閨怨之外:以實力論台灣女作家的小說〉,《霧起霧散之際:文學卷冊》(台北:天下文化,2017),頁176-204。
③ 陳培豐在他最近的研究中指出,從「閨怨」到「港歌」的變化反應了台灣人經受「連續殖民」的幽怨心情,見《歌唱台灣:連續殖民下台語歌曲的變遷》(台北:衛城,2020)。惟須注意的是,〈港邊惜別〉是少數在戰前就出現的以「港」為背景的台語歌曲。
撰文|鍾秩維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系畢業,在同一學校的台灣文學研究所取得碩、博士學位。現為台大文學院「趨勢人文與科技講座」博士後研究員。研究興趣為台灣文學、抒情傳統與當代批判理論。著有博士論文《抒情與本土:戰後台灣文學的自我、共同體與世界圖像》(2020)。
攝影|安比

■ 2021六月號|440期 ■
蕭麗紅打造一座溫潤明淨的布袋大觀園,寫貞觀刻骨銘心的初戀,四十年來讓多少讀者著迷,記載台灣庶民生活,在熾熱未歇的鄉土文學風潮之中,寫出最醇厚的地景人情。紀念《千江有水千江月》四十週年,本期專題從小鎮風情出發,看虛構與真實地景交會,作家共讀蕭麗紅,深入台灣鄉土文學脈絡,看小說中的民俗,從四十年後回望戀愛觀的變遷,並探究中學教育如何理解蕭麗紅的性別議題。這座小鎮巷弄曲折,有多少屋舍就有多少小徑,但終究會通往千江映月的廣闊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