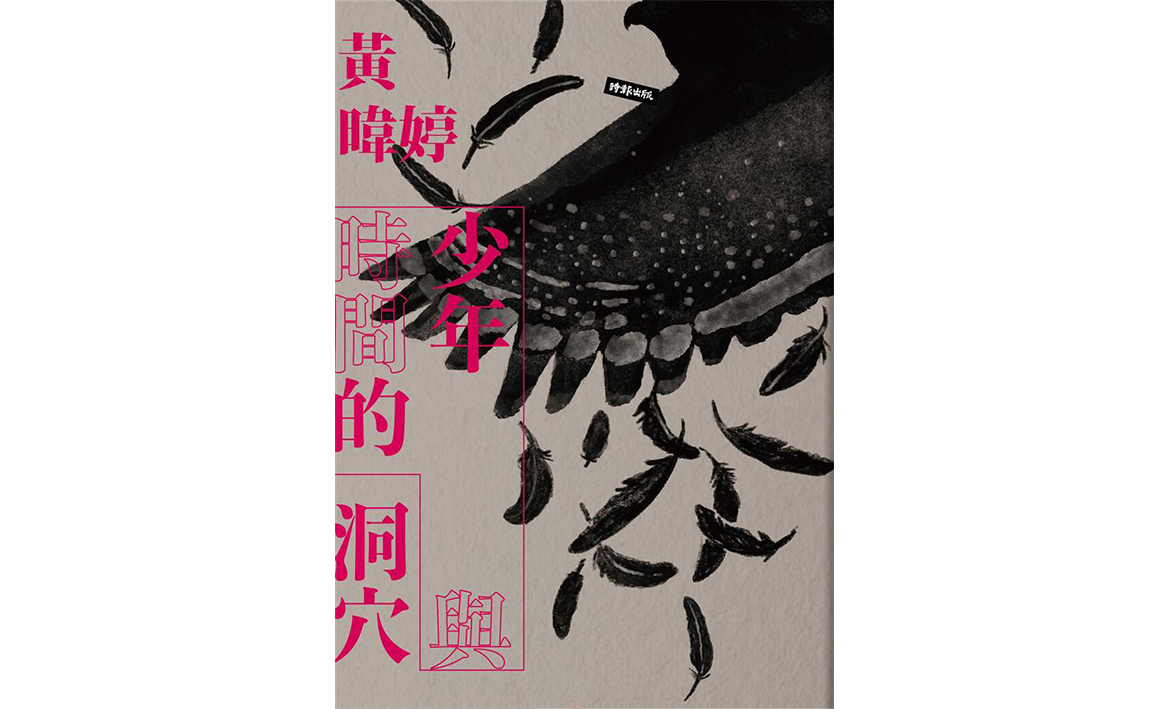如果你曾經被《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裡火車站那黑色皮箱的交運者是誰所誘惑,那你就不得不佩服《少年與時間的洞穴》只用一個謊言和一個未寫的故事,就把讀者你步步懸釣,既沒有看著編輯阿基和小說家莉卡說他們讀到的一個個與將寫的小說無關的故事內容拂袖而去,也沒有因為搞不清楚阿基愛戀的「她」是人是鬼、莉卡遇見的灰哥明明就是小說裡長大後的少年朗嘛?可跟少年朗在一起的女人的祖母又是少年朗阿公的初戀情人。然後少年朗又同時出現在阿基和莉卡的生活場景中……等等諸如此類真實的虛構給嚇跑,足見黃暐婷說故事的魔性實力非同一般。
一位編輯「說」了一個謊話、一位作家「想寫」一個故事,作家「聽信」了謊言,所以謊言成了真實;編輯等待作家想寫的故事,故事卻在別人寫的小說裡。這打破時間連續性的因果序列,後現代空間並置的互文性,又一個確確實實的〈一千零一夜〉——現在、過去、未來是敘事而生的此在、是書寫成真的唯一現實,那自以為創世的寫作者,不過是「我說」的故事裡每一個說故事的我。哆啦A夢中原本只能穿越平行時空的任意門,因為放入了時光機,便再也沒有不能同時窺看的歷史與未來。黃暐婷的《少年與時間的洞穴》一開始便向伊羅塔.卡爾維諾表達了深切的敬意。
如果你曾經被《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裡火車站那黑色皮箱的交運者是誰所誘惑,那你就不得不佩服《少年與時間的洞穴》只用一個謊言和一個未寫的故事,就把讀者你步步懸釣,既沒有看著編輯阿基和小說家莉卡說他們讀到的一個個與將寫的小說無關的故事內容拂袖而去,也沒有因為搞不清楚阿基愛戀的「她」是人是鬼、莉卡遇見的灰哥明明就是小說裡長大後的少年朗嘛?可跟少年朗在一起的女人的祖母又是少年朗阿公的初戀情人。然後少年朗又同時出現在阿基和莉卡的生活場景中……等等諸如此類真實的虛構給嚇跑,足見黃暐婷說故事的魔性實力非同一般。但是,正如伊羅塔.卡爾維諾並不只是為了闡述閱讀理論而寫小說,《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看不見的城市》其實更深刻地以文學話語解構了政治、歷史、文化裡的權力關係與運作模式。《少年與時間的洞穴》的兩條情節軸線以「時差調整」來開啟敘事,顯然是要通過時間意識的改換,將謊言、故事與記憶、歷史的傳統虛實界線泯除於同是符號指涉建構成的認知中。作者明言「調快一小時」這個小小的看似因應日光節能的時間節縮,竟然涉及了因為時區劃分 (即與日本同時區或與中國同時區)衍伸出的國族歸屬問題。是以作者在少年朗這條敘事軸線中,以阿基編造虛構的女朋友「她」變成真實存在的寫虛成實,來呼應並涉入台灣歷史與政治論述在各式話語符號裡的變造與操控。例如:離開原鄉和Ama的少年朗所不斷見證的資本主義社會那虛假的文明景觀(老婦人夜宿的樣品屋)、部落殺猴與都市掠奪的比較、文學編輯對於作品出版與商業利益的掙扎以及各個人物間點染的各種生存權力關係,所謂的「時間的洞穴」竟是繁華都市裡的一座廢墟,這新時與舊時並置的世界,考驗了人在時間(歷史)意識與認知上的選擇,所以當不同政治勢力為了取得對歷史的現代詮釋權而爭論不休時,時差不過是人們生活裡一些些的不便,在習慣之後沒有人在乎或記得這被偷走的一小時究竟失去了甚麼。
通過符號建構世界此一現代主義以來的哲學基礎和美學形式,《少年與時間的洞穴》由於將小說中各個文本內容改以讀者(即通過阿基和莉卡這兩位閱讀者的講述)的概括方式陳述,而不以原文徵引方式呈現,遂更直接取消了作者風格、品味等個人特質或經驗在作品中的賦義位置,作為主體的作者,反而必須仰賴其書寫的符號方得以建構出自我的面貌,真可謂極致地宣告了作者已死的閱讀理論核心。但這同時也使得小說中諸多的故事失去了呼應並深化情節意涵的隱喻功能,它簡化了作者欲藉時差探索歷史文化意識的創作主題,使那作為所有詮釋根源的照片裡的女子(我姑且臆度其為國族母體的象徵)以及少年朗完成阿公對初戀情人的責任(即身世根源的追索)這一條小說中真正想要提出的關於「我是誰」的探問,反而成為陪襯以虛為實之資本主義社會的枝節,和人物不經意間發出的政治牢騷而已。
伊羅塔.卡爾維諾在《如果在冬夜,一個旅人》裡說:「如果我們假定寫作是用來超越作者的極限,那它只有被單獨一人閱讀並流過他的心思線路時才始終有其意義。只有某個特定的個人的閱讀能力才可證明那些寫下的東西具有書寫的力量,一種根據超越個人的東西所建立的力量。只有人可以說:『我讀,故它寫』,宇宙才會自行表達它本身。」時間本就是以一種先驗的形式主導了我們對於事物的認知,在《少年與時間的洞穴》裡,黃暐婷不聚焦於時間本身所指涉的生命價值與維度,一開始便藉莉卡的小說《白象經過的村莊》之口將時間徹底封存,把世界視為一個在時間靜止下,方能被見知的一個個湖面上的影子,而這影子竟是現代文明裡人可以擁有的唯一真實。
無論是在夢與醒裡翻轉人生的「夜裡的敵人」,還是渴欲所愛的「長長敲門聲」,你,讀者,就是那位嗜故事的國王,唯有在一個又一個故事裡,你才得以確立了自己的權力,完足了自己的世界。雖然總有人說:無論多精彩,也只是個故事而已。不過,我相信讀者—你—在閱讀《少年與時間的洞穴》時,這些為著記憶情感而痛苦的人生與因著遺忘才有快樂的生活其實輕盈的一點都不輕鬆。
還在舊時裡的我(抑是你),既然在講述書寫中存在的如此真實而虛無。你總會厭倦孤獨穿越的任意門裡無數的自我和奇幻的旅程,那麼,別擔心,只要交出自己的時間,和即將長大成人的少年朗一樣「把錶轉快一圈,這樣一來,你的時間就和其他的時間一樣了。」

《少年與時間的洞穴》,黃暐婷,時報出版
一九三七年的十月一日凌晨,台灣的時區改成跟日本本島同步(UTC+9)一九四五年,因為日本戰敗,台灣的時區又改回跟中國同步的西部標準時(UTC+8)
你曾經想過嗎?時間,和時差,其實都是人為的?你曾經想像過嗎?不經意說出的謊言,也可能自己生長出一片平行時空?以短篇小說《捕霧的人》驚艷文壇的黃暐婷,首部作品獲吳明益專序推薦,形容「哀而不傷,是暐婷作品的共同特質」,蟄伏兩年多,這位女作家交出了重量級長篇之作,而且是一本讓人翻開就停不下來的奇妙小說。
文|許琇禎
一九六三年生。台北市立大學中文系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文學博士。曾獲時報文學獎小說獎、聯合報文學獎小說獎、聯合文學小說新人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專長文學理論及現當代文學批評,著有《解嚴前後台灣當代小說綜論(1977-1997)》、《林耀德小說研究》、《嚴歌苓小說研究》、《沈雁冰文學研究》、《朱自清散文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