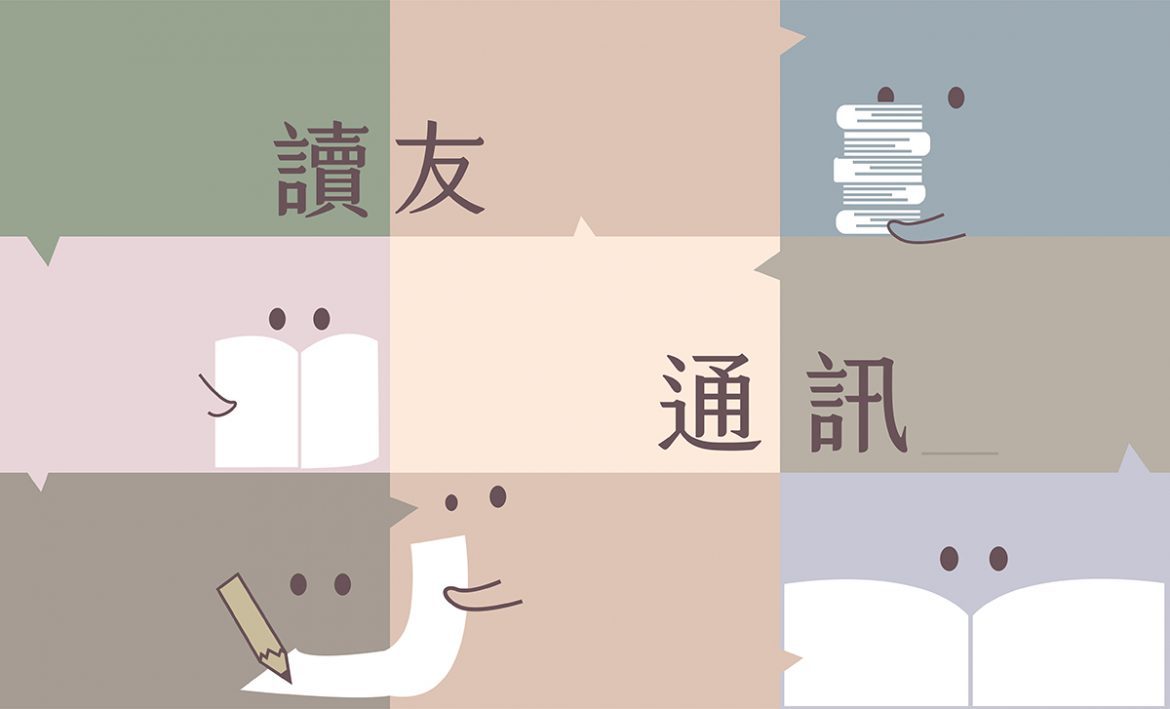Dear 讀友:
你是否有特別疲倦想躺下睡個午覺恢復精神,卻意外做了可怕的惡夢的經驗?
我剛從這樣的慘況中醒來,夢中與FY約好要去看場演唱會,在現場苦候許久卻仍等不到他的我意外捲入一場流血衝突,用盡腎上腺素逃跑到連鞋子都在不知不覺間遺失,而且發現無論怎麼打電話都無法連絡上他,正想找個地方坐下來大哭一場時手機卻突然接通,從白噪音的那一端穿越而來的是FY的聲音,他說找了兩天完全沒有我的消息,放下心來之後我抱著他不斷大哭,夢境的最後,只記得自己嚷嚷著:「我要換手機!」。
安心又疲倦地從暖呼呼的被窩中醒來,窗外已是薄暮時分,呆呆看著日本冬季特有的天色,一邊拿起手機聯繫FY,他打趣地笑話我的夢根本是手機的業配廣告,但我們同時都認可這個業配夢推坑力十足,在這個沒有手機就失去所有聯繫的現代,連接不到重要他人實在是一件太可怕的事情。(該聯繫一下夢境百貨公司求償嗎?)
想到上一封信談到扁平化會讓世界各地的人模糊成同一張臉孔,這次的夢卻又仿若警鐘提醒與他人連結的不可或缺,如果我持續被困在那處精神時光屋之中,無法與任何人取得聯繫,那「我」會變成什麼模樣?由此反推形成「我」的要素裡是否必定有他人的影響、評價和投射呢?究竟「自我」到底是什麼?又該被什麼所定義?想與你分享最近讀的「基姆」,吉卜林在書中描寫出生在印度的英國少年基姆不斷追求自我認同的故事,也以此拿下了諾貝爾文學獎。
基姆雖有一副白人的外表,卻擁有純粹的印度靈魂。從小在市井長大的他能隨著情境需要自由切換裝扮及語言,如魚得水地佔盡他人便宜,也從沒有思考過有任何不妥之處;直到他意外遇見來自北方的喇嘛,已位居住持的喇嘛獨自一人跋山涉水來到印度,預備去尋找一條傳說中的河流。幾乎沒有謀生能力的喇嘛吸引了基姆的注意,他決定成為喇嘛的徒弟並追隨這位逐夢者的旅程,同時也想起了父親的遺言「去尋找綠地上的紅牛」,基姆彷彿也有了一個使命,於是師徒兩人踏上了追尋的道路。
過程中當然有許多意外起落,遇上了英國的軍團而使基姆不得不接受西方教育的洗禮,然而隨著他逐漸成長為青年,接觸了殖民地檯面下複雜的交易,他也不斷比較西方與東方的哲學和信仰,書中不斷出現他對自己究竟是誰的疑惑,以及他選擇要成為哪一個自己的思索。
「他習慣了印度人的冷漠,但是身處白人之間帶來的強烈孤寂感讓他深受折磨。」
「基姆望著星星在寂靜濕熱的夜色中一顆顆升起,直到後來在佛桌旁睡著.那晚他在夢中說的都是印度語,沒有任何英文⋯⋯」
「基姆一直是用印度語思考,可是他感覺到一陣戰慄,像是泳者遭鯊魚追逐、拼命要從水裡逃生那樣掙扎,他內心竭力擺脫將吞沒他的一片黑暗,並用英語默背九九乘法表當作護身咒語。」
曾有研究顯示同一個人說不同的語言時,人格特質會隨之改變,人在異鄉感受特別深刻,說日語的時候我不會那麼強烈主張自己的意見,更傾向於妥協和維持關係的和諧,光只是置換語言就能讓人產生強烈的孤寂,更別提失去雙親的基姆成長中沒有典範可追尋,獨自摸索自我的真實樣貌是一條多麼艱辛的道路。讀到後記才發現吉卜林也出生於印度,他一定投射了某種程度的自己才能準確捕捉那份惶惑。
不過隨著年紀增長,我感覺到內心深處如核心般的東西越漸穩固,不再輕易隨他人評價起舞也甚少動怒,但要說我全然了解自己恐怕也未必,這應該也是莎莉魯尼的「正常人」和「聊天記錄」如此深受大家喜愛的原因,隨著人生喜怒哀樂高潮迭起,不斷更新對自己的認識,原來這件事早已放下、原來那件事仍耿耿於懷、原來對家國有如此大的展望,總之我還算滿意目前的自己,你呢?

《基姆》,吉卜林,聯經出版
主角基姆自小在當時隸屬於印度的拉合爾長大,他是英國人,但晒得很黑,就跟印度人沒兩樣,他講起英語劈里啪啦,但他偏愛講本地話。照顧基姆的那個女人堅持他得穿歐洲人的服裝,不過基姆發現做某些事時,換上印度服裝或穆斯林的服裝比較方便。基姆的綽號是「世界之友」,他有結交各界人馬的能力:他在夜裡為光鮮亮麗的時髦年輕人辦事;在屋頂上偷看婦女的居家生活,他與苦行僧也很熟。當然,基姆很清楚,那些都是不能曝光的祕密,因為他從會講話開始,就見識了世間的各種邪惡。
文|Why Not Reading
Why Not Reading 是我們夫妻的閱讀紀錄。我是比較常發文的 SW,當過近十年中學教師,現職為 FY 的小小書僮。喜歡關注人生百態,目前很幸運擁有大把時間思考下個階段的目標。